DBC·皮埃尔至今共创作了七部作品,包括小说写作指南《释放蝙蝠》(
Release the Bats
)与获得2003年布克奖的《维农少年》。在布克奖的颁奖典礼上,皮埃尔(原名彼得·芬利,1961年出生于澳大利亚)许诺,他将把奖金给那些自己过去居无定所时曾欺骗过的朋友——皮埃尔承认,当时的自己是个骗子兼瘾君子;他笔名中的“DBC”取自“卑鄙但清白”(Dirty But Clean)的首字母。
皮埃尔在位于剑桥郡的家中接受了我(指本文作者Anthony Cummins)的采访,他最新的作品《在多巴胺城发生的事情》(
Meanwhile in Dopamine City
)就创作于此,这本书是一本反乌托邦式讽刺小说,讲述了一名鳏居的下水道工人在数字创新狂潮的时代挣扎着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的故事。
《卫报》:为什么会想到去讽刺数字科技和互联网,也就是你书中所说的“电网”(the grid)呢?
DBC·皮埃尔: 我也想写一本以蝴蝶或者其他东西为主题的书,但当下发生的这一切太让我生气了。大约五年前,出于“脑化学”“暴民文化”以及“利润动机”等种种原因,“在网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这个概念开始朝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发生改变……我并不是一个恐惧新技术的人,我只是认为,这些网络技术背后的东西极其令人担忧。我们奔走相告,说着自己突然拥有了发言权,但实际上互联网却使人变得更加幼稚了——人们在社交软件上仿佛都自动变回了青少年。他们是这么适应网络环境的:与事实相比,我们更喜欢的是想法,所以我们会自动无视掉大量的事实。作为一名小说作家,我感到很气馁,因为这太荒谬了……但平心而论,放在20年前,创作讽刺文学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卫报》:与写作《维农少年》时相比,你是否认为自己现在的创作资源更加丰富呢?
DBC·皮埃尔: 这是肯定的。我在创作现在这本书的第一年犯了个错误,我当时以为,我只需要畅想5年后或者10年后的生活就可以了,于是我在书里写了一些很酷的新发明。但到了那年的年底,我书中的“新发明”都已成了明日黄花。
《卫报》:在书的开头,主人公在打了女儿后,发现自己被打上了施虐者的烙印。
DBC·皮埃尔: 在主人公朗尼生活的世界,人人都愿意给他人第二次机会。我现在的人生也得益于第二次机会:我是在得到了他人的宽恕,并且获得帮助重新振作之后,今天才能够在这里与你对话。我相信给人第二次机会是正确之举,但会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的人很容易因为一个错误而一蹶不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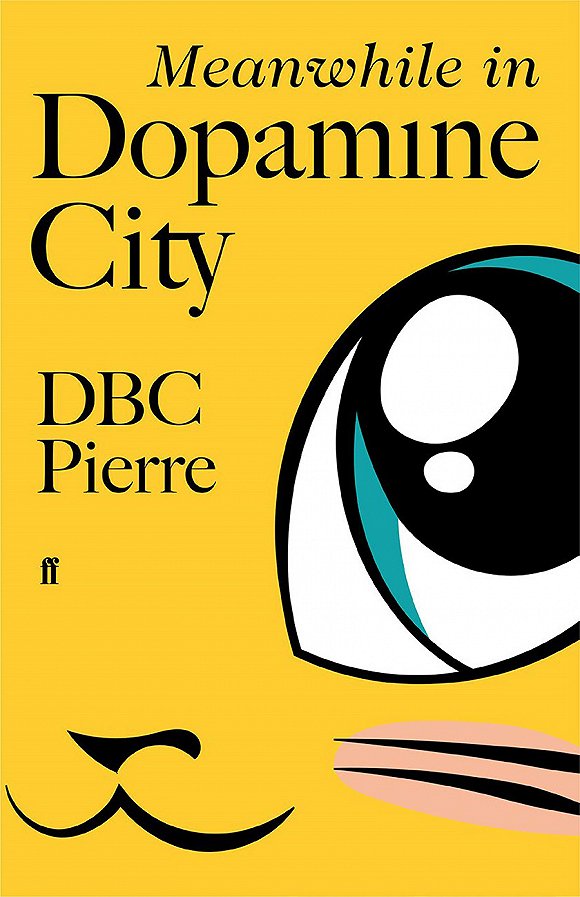
《在多巴胺城发生的事情》
《卫报》:朗尼担心自己的女儿成长得太快了……
DBC·皮埃尔: 他(朗尼)就像一台康懋达64电脑(Commodore 64,瑞典公司康懋达国际于1982年1月推出的8位家用电脑),他的编码跟当下的电脑系统已经不匹配了,现在的孩子用的是Windows 10的系统,所以他必须弄懂新的编码。在风云变幻的数年里,他一直身处地下隧道之中,跟下水管道打交道——此处的“隧道”具有象征意义,我安排他身处真正的隧道之中,好让这种象征意义得到体现——现在他又被迫回到了地面上(因为他失去了工作),并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他开始焦虑不安,当然,这无可厚非。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心情,但在我心中,朗尼的编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善良、高尚,而且更加自由。
《卫报》:当朗尼第一次拿起智能手机时,书里的文本分成了左右两栏。你在这里花了不少心思:你得一边在左边栏继续叙述故事主线,一边在右边栏铺陈大量的新闻消息。
DBC·皮埃尔: 创作这个右边栏花了我18个月!我只能想到这个方式来呈现注意力一分为二的体验。但也许有人接受不了这种形式。我在初稿中本来想通过这种设置来给读者的大脑“重新搭线”:初稿中的右边栏跟情节密切相关,所以你得想清楚,是要先读完全书的左边栏,再返回来读右边栏,还是直接把左右两边放在一起读,但这样一来叙述的连贯性就被破坏了。在最终成书的版本中,你则完全可以一瞥或是无视右边栏的新闻消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左边。这是编辑给我的建议,我觉得效果挺好的。为这本书设置页码简直是个噩梦:一开始分栏里的一个逗号就能让我们错位200页。现在这该死的书终于要出版了,大家都很开心!
《卫报》:你目前在读什么书?
DBC·皮埃尔: 我喜欢19世纪早期和20世纪的作品。那个时代的描写比现在细腻得多,作家常会用一到两个长句来精确描绘某种感觉。而现在大家都只会发表情包……最近班菲·米克洛什的“奥匈帝国命运三部曲”的第一部《They Were Counted》让我爱不释手,这本厚重的历史传奇小说讲述了一名特兰西瓦尼亚伯爵一生的境遇和爱情故事。还有肖沙娜·朱伯夫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我虽然在写这本新作时没有读这本书,但现在看来,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佐证了我所叙述的数字科技的危害。
《卫报》:小时候的你是一位怎样的读者?
DBC·皮埃尔: 我是个幸运的孩子,因为我的父母每晚都会给我读睡前故事,这让我很小就拥有了丰富的想象力。我的父亲是个很乐观的人——他给我读的都是《小火车头做到了》(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这样的故事,对我颇有激励作用。后来能够自己阅读时,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少儿冒险故事,就这么一直到了11岁。11岁的我也许是觉得手头上的书都太薄了(它们的结局总让我意犹未尽),所以去买了一本厚重精装版的伊夫林·沃的《衰落与瓦解》,这一步对我来说很关键,因为这本书讲述的是真正的成年人的生活,使用的也是成年人的表达,而且与《哈迪男孩》(
The Hardy Boys
,少儿读物)比起来,里面的新奇事物简直让我目不暇接。
(翻译:黄婧思)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