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关注美国诗歌的读者在上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了露易丝·格丽克,其余文坛人士大多把她不久前获得诺贝尔奖当作一个惊喜。这也难怪。她并没有特别的话题性,也不算特别有国际影响力。就像她后期作品中出现的那些更悲伤但更聪明的成年人一样,她似乎可以保持自己的节奏,并远离一切。这种态度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她成功的条件,她的作品是严肃的,往往简洁、内省、令人不安,有时则令人振奋。就像与她同类的那些作家一样,她身上也有矛盾之处。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她的12卷诗集(和两本小册子),它们可能看起来几乎都是一个整体。不过,再读它们,分化就会跳出来。格丽克曾说过,她试图改变和挑战自己,甚至每本新书都要反其道而行;如果你读得足够深入,你就能看出她在这一点上的坚持无比正确。
不要从头开始,把《头生子》( Firstborn ,1969)作为入门作品,最好先读《沼泽地上的房屋》( The House on Marshland ,1975年)和之后的几卷诗。这些优雅明快的作品,为我们描绘了在一个真相永远残酷暗淡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女性或女孩。格丽克笔下的格莱特在逃离女巫后,无法停止想象哥哥差点死在其中的炉子,她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拯救他。一首名为《我的黑衣服在这里》(Here Are My Black Clothes)的诗开始是这样的:“我想现在不爱任何人比较好/与爱你比起来的话。” 《情诗》(Love Poem)谴责情人或前任:“难怪你会变成这样,/害怕血腥,你的女人/像一堵又一堵砖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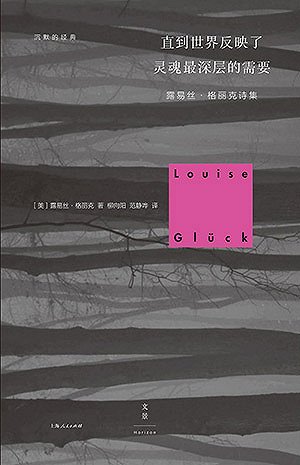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 柳向阳/范静哗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5
格丽克早期的文风并不总是那么凄凉,但她在作品中描述了许多人、许多困难的家庭、许多成年人的艰难选择,而不是堆砌自己生活中的细节。《阿基里斯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Achilles ,1985)扩大了她的神话和场景、格言和见解的主题范围,但并没有减轻悲伤的情绪:一个市场上堆放着橘子的梦境幻象,显然是一个孤独女孩的避难所,最后:“于是就这么定了:我可以在那里度过一个童年/这就意味着永远孤独。”
格丽克的父亲参与发明了常用于制作工艺的X-Acto美工刀,这是对格丽克诗歌下笔精度的绝妙隐喻。她在长岛的青春岁月充斥着饮食失调带来的意外,格丽克没有上大学,而是在大量的心理分析咨询中度过了那段时期。“我学会了像心理医生一样倾听,”她在《阿勒山》( Ararat ,1990)中写道。这卷诗集把家庭故事放在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不可信的说话者》(The Unreliable Narrator)等诗中长长的、几乎是聊天的场景,可能会让那些早年生活困难的读者产生共鸣。《一则故事》(A Fable)改编了所罗门王的传说:“假设/你看到你的母亲/在两个女儿之间徘徊:/ 你能做什么呢/ 为了拯救她,除了/愿意去毁灭/你自己?”如果说这些诗是忏悔的话,那它们是自觉又自责地把可能毁掉生命的创伤当作事实来陈述的:“我的儿子很优雅,他有完美的平衡/他不像我姐姐的女儿那样争强好胜。”(《表亲》[Cousins])
这些自我审视仍然是一些读者最喜欢的诗歌,但对另一部分读者来说,它们就像是格丽克获得普利策奖的《野鸢尾》的前奏。《野鸢尾》的大部分抒情诗都有非人类的叙述者:花草、苔藓、树木和上帝。诗人通过这样的面具,代表整个世界对造物主说话。“你救过我,你应该还记得我。”(花瓣和叶子是很好的天堂般的回应者,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不适合任何一个人。)《雏菊》(Daisies)甚至错开了诗意怀疑论者的脚步,质问格丽克按照时间去记录的感情是否重要:“继续吧:说说你在想什么。花园/不是真实的世界……非常感人,/当看到你正小心地/接近。”格丽克在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证明与理论》( Proofs & Theories ,1994)中写道,她试图使自己的每本书都能从上一本中吸取一种力量:她从未停止对自己的要求。在神话抒情、自传和田园寓言(会说话的花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后,她转向史诗和喜剧。她接下来的作品——从《草场》( Meadowlands ,1996)到《阿维诺》( Averno ,2006年)——围绕着婚姻的解体、中年重建生活的尝试、旅行者和继承人的史诗之旅,以及但丁和荷马笔下的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有时甚至运用了突降法修辞。“我想我的生活已经结束,我的心已经破碎。/于是我搬到了剑桥。”《新生》( Vita Nova ,1999)的结尾这样写道。从此,她把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当成了自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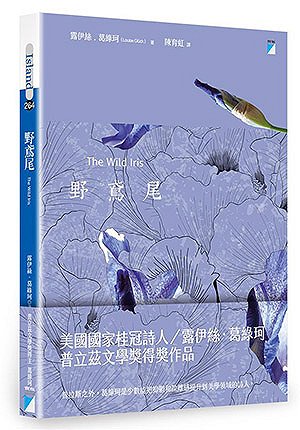
《野鸢尾》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 陈育虹 译
宝瓶文化 2017-2
此时她已完全成名,捧得国家图书奖,在耶鲁大学工作,还有许多其他荣誉傍身。其他诗人可能会专注于投身公众活动,而损害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格丽克抓住了这些机会,她担任耶鲁青年诗人大赛评委,2003-2004年担任美国桂冠诗人顾问,也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新的渠道。《村居生活》( A Village Life ,2009)发生在一个与意大利北部并无二致的牧区环境中,农民和工匠保持着一个不温不火的时代的爱与哀愁。“年轻人搬到城市,但又搬回来。/按我理解,要是留下来,/那样,梦想也伤不到你。”她最近的新诗集《忠贞良宵》( 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 ,2014)——也是她第一本收录了许多散文诗的作品——讲述了一个虚构的老年作家的生活,从最早的青年时代开始,“我可以说话,我很快乐。/或者说:我可以说话,因此我很幸福。”但这样的幸福不能停留:成年后,“他躺在书房冰冷的地板上,看着风搅动书页,把写的和没写的混在一起,结局就在其中。”(《开着的窗》)
格丽克的诗面对的是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诗人所否认的真相: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衰老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即使是最幸运的成人,失望也会渗透他们的生活。她不是一个你读来给自己打气的诗人,但她是一位智慧的诗人,她的宣言、她的决定、她的结论,随着诗歌的推进而相互建立和置换:即使是最尖锐的主张,也需要它们的诗性框架和对比。
格丽克的书看起来既充满深意又天马行空,充满思考的同时也充满了勇气和魄力。如果说她最早的成功与西尔维娅·普拉斯相呼应,那么她最近的成功则超越了美国诗歌,达到了安东·契诃夫的忧郁慷慨、爱丽丝·门罗的视角多变。所有的诗人都来自某个地方,没有一个诗人能代表我们所有人。不过,我们可以说,格丽克平实的句子和广阔的视野涉及到许多人的共同经历:感觉被忽视,感觉太年轻或太老,以及——有时——热爱我们发现的生活。
(《望远镜》及部分诗歌译文摘自《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柳向阳/范静哗 译)
(翻译:李思璟)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