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些小贩吆喝着经过茶馆时,不想回家吃早饭的茶客便摸出几文铜钱,叫小贩把点的小吃端进来,屁股不用离开座椅,早餐便已落肚。那时成都人最常吃的早餐,无非是汤圆、醪糟蛋、锅盔、蒸糕、糍粑、油条等,出三五文便可打发肚子,小贩们担一副挑子,一端是火炉,一端是食品佐料和锅盆碗盏,简直就是一个流动厨房。”
这是历史学家王笛笔下1900年1月1日的成都早晨。彼时的中国正值风云变幻之际,义和团遍及华北,一个英国传教士在世纪之交的夜晚被杀死,腥风血雨就要来临,但远在成都的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清晨还是一碗热茶。这种悠闲的态度被同时代的精英所鄙弃,后来也为长江下游流离失所的难民所恨恼,乱世里不容有此无意义的慵散。
然于微观史的研究而言,意义就暗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下。自上世纪90年代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起,王笛便将目光转向了小人物的日常。他曾经调侃,如果百年前的成都茶客听说这位“小同乡”要为他们撰写历史,他们一定会用本地方言把他嘲弄一番:“你莫得事做,还不如去洗煤炭……”但如果我们把历史置于 “显微镜”下去观察便会发现,这些小人物拿起茶碗茶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以及国家文化的浪潮中做出了“弱者的反抗”,为千城一面的都市生活保得一点地方特色,而像“袍哥”雷明远那样在廿四史里不具姓名的人物,恰恰能让我们一探当时社会的运作。
从早期充满各种图表和数据的《走出封闭的世界》,到后来以叙事为主《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王笛不断缩小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叙事的笔调来讲述有血有肉的历史。诗人流沙河曾写道:“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乡愁者的心窝。”王笛把自己比作一只“四川蟋蟀”,为成都唱了近三十年的歌。最近出版的《显微镜下的成都》是这首“蟋蟀之歌”的汇总,也是作者学术转型的实录。如果我们也用“显微镜”的方法来阅读这部著作,便可从其个人的学术之路中窥见70年代高考恢复、80年代国内史学研究的社科倾向以及90年代留学热潮。借新书出版之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连线王笛进行了一次采访,与他聊了聊20世纪中国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城市公共空间的沉浮、国家文化的兴起、“城市形象”问题以及微观史在中国的近况。

历史学家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
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王笛不断强调“大众”在史学中的重要性:一是史学界的研究应当重视微观史的工作,在帝王将相之外复活属于平民的历史细节;二来,在写作与阅读方面,专业史学著作应当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既然微观史写的是大众历史,那么应该尽可能地探索一种平易近人的写作方式,邀请更多读者参与阅读,而非以专业性制造门槛。在聊到当下城市的状况时,王笛同样坚持了“大众”的视野,认为城市应当保障人们街头谋生的权利。
此外,《显微镜下的成都》还首次集结了王笛对麻将的研究。通过分析2000年成都的一起麻将官司,王笛探讨了社会主义时代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共同认同的道德规则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案例中小区居委会的处境也揭露了国家文化全面介入生活后所面临的尴尬——居委会为居民提供打麻将场所有违“禁止赌博”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却是其“丰富居民业余生活”的职能所在。
01 清谈误国?茶馆并非浪费时间的无用之地
界面文化:20世纪初的精英阶层对泡茶馆、打麻将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不过是蹉跎时光、磨人意志。这类态度在今天不独属于精英,一些普通人也以此来批评茶馆或麻将,但也有人开始反思这种态度,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王笛: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运动。过去在传统社会,戏曲之类的大众娱乐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管理模式随着晚清以来的现代化传入中国后,许多精英就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认为它是落后的,是阻碍现代化的,要加以改造。
民国时期,胡适等精英知识分子把打麻将同吸鸦片、写八股文和裹小脚一起,列为四害,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对待茶馆的态度也是一样。从晚清起,地方精英和官方都认为泡茶馆是浪费时间。抗战时期,从长江下游地区撤退的难民到成都一看,非常吃惊,国难当头,怎么还在这里喝茶?于是就批评他们“清谈误国”。1949年以后,提倡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娱乐,根本就不鼓励开茶馆、坐茶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茶馆基本都关掉了。
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管控逐渐松弛,茶馆又在成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了。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不过五六百家, 2000年左右有4000多家,前年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数量更多达9900余家。这当然和成都的地域扩展有关,但也很能说明茶馆在近40年里的发展活力。
成都在历史上是一个消费城市,以小商小铺和手工业为主。1949年以后方向转变,成为生产型城市,发展大工业,改革开放又是一轮新的城市定位和规划。经济发展以后,人们开始考虑城市的多样化以及生活品质的问题,而不是要把所有的城市都打造成千篇一律的工厂,催促所有人去拼命赚钱。总的来说,中国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在20世纪日趋收紧,现在有更多人接受,工作和享受生活是可以共存的,不是说享受生活就一定是要挨批评,我们现在的反思是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

老人们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打牌。来源:王笛2015 年秋摄于成都郊区彭镇
界面文化:这些批评的背后隐含了一个观念,即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茶馆看似没有什么经济产出,因而无用。但从你的研究可以看到,茶馆在信息交流、社区认同等方面的作用非常大,对一个正常社会的运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历史事实对当下有什么启示?
王笛: 晚清民国时期以来,我们就对茶馆有误解,认为它只是一个休闲和浪费时间和金钱的地方。但是事实上,茶馆不只是一个休闲空间,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微观世界,从这个小空间可以看到整个大世界的运作。
认为茶馆里都是无所事事的人,也是不对的。我在研究民国时期的茶馆资料时发现,当时茶馆里被认为有两种人,一个叫“有闲阶级”,一个叫“有忙阶级”。有的人在茶馆里面休闲,但有的人是谋生,这两种身份可以随时互相转换。茶馆像个市场,小商小贩在那里卖东西,还有掏耳的、算命的等等,是三教九流各个阶层的聚集地。从事特定行业的人有他们固定的据点,比如做丝绸生意的、做大米生意的、卖瓷器的都会到某个固定茶馆去见同行,谈生意。有时候茶馆可能还是人力市场,人们可以到那里去雇佣工人。
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茶馆》第二卷里面我讲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被称为“皮包公司”的商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就拎个皮包在茶馆里做生意。改革开放初期,成都的物资交流会都是在茶馆里面定期举行的,尽管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形式被淘汰了,但茶馆依旧有信息交流的作用。现在成都很多读书会、沙龙也在茶馆里面举行,大家并不是在那里浪费时间。
茶馆也是一个会客厅。一些人因为共同的兴趣聚集到茶馆来,还有像袍哥这样的社会组织,他们没有自己的据点,就把茶馆当作自己的活动地点。今天的成都人见朋友、见同学也还是会到茶馆去,它是一个社会交流、产生自我认同的场所。
刚才我们讲到抗战时期的难民批评成都的生活方式,当时有个成都人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他说,我们不主张也不喊“茶馆万岁”,随着社会的发展,茶馆自然而然会被淘汰,我们不需要专门去要消灭它。这个作者为茶馆辩护,可是他也认为茶馆是旧的东西,迟早要消亡。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现在成都的社会已经这么现代化了,茶馆不但没有减少,没有衰落,反而还在继续发展。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式的咖啡馆、奶茶店,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地位可能面临着挑战,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措施也会冲击茶馆的功能,但任何人都很难预测茶馆的未来。

茶馆里的堂倌。来源:图虫
02 打造宜居便利城市要靠“管理”而非“禁止”
界面文化:“有损城市形象”是反对街头小商业的理由之一。一些人认为流动商贩会影响城市的整洁、美观,损害现代都市形象,但20世纪初的成都人对占道、噪音等问题表现得十分宽容,那时的人们怎么看待“城市形象”问题呢?“城市形象”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与你所说的“国家文化”有什么关系?
王笛: 过去的中国没有“城市形象”的概念。传统的中国城市没有市政府、警察等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而是通过街坊、保甲、会馆等社会组织进行城市自治。城市也是自然形成,从布局到外貌,都没有事先设计过。直到清末新政,才从西方、日本的城市管理那里引入了交通、卫生等概念以及警察系统,市政府到上世纪20年代才出现。
晚清、民国及1949年以后的城市管理有一个共同的来自西方的模式,即由国家来设立一套标准。过去地方上的城市没有这些标准,标准的推广意味着城市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形象”的概念才慢慢出现。在晚清,不少地方精英就不断地鼓吹,成都是四川的首府,首善之区要做出一个好榜样,街道要干净整齐,行人要守规矩。最开始的限定还比较松弛,只在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要求不摆摊,不怎么管小街小巷,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严格。所谓国家文化,就是以国家力量来推动这种整齐划一的城市改造。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城市管理都是这种思维方式,按我的观察,可以说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是说城市不应该进行管理,而是要看管理什么地方、怎么管理。交通、卫生、噪音等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但“一刀切”是不对的,需要更细致的办法。泰国的曼谷、清迈也是很现代化的城市,那里的夜市熙熙攘攘,却不见遍地垃圾的情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家文化其实可以把城市朝着便利、宜居的方向打造。说到底,这是“管理”的问题,不是“禁止”的问题。把别人的摊子砸了、车没收了,这样粗暴的执法才会引起市民反感,损害城市形象。
我认为一个城市形象好不好,取决于它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也取决于本地居民对外来者的态度。城市需要多元化,可以有高档的,但也必须提供低档的。低收入群体需要依靠街头来谋生,为了城市的漂亮、整齐、干净而驱逐他们,是一种错误的美学。前段时间成都率先允许占道经营,这是个很好的态度,但我不希望这只是针对目前经济状况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成为一种长期的政策。

俯瞰老成都。来源:罗林· T.钱柏林(Rollin T. Chamberlin, 1881—1948)1909年摄于成都,Beloit College Archives
界面文化:说到成都率先解绑街头经济,你认为这里面有你所谈的文化的“连贯性”吗?
王笛: 我认为是有的。过去我们一讲到现代化,都爱强调变化的部分,仿佛什么都变了:文化变了,经济变了,生活方式变了,管理方式变了,都在变。但文化有其连续性,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有时候表面上看是变了,但它的内在没有消失,只要有一定的土壤,它就会重新冒出来,街头经济正是如此。
我一直强调,中国过去的农村和城市都有经商传统。农民在农闲时做点小生意,城里头更有很多的小商小贩,他们知道怎么做买卖。1949年以后什么都是集体或者国家所有,自主性被压住了。只有等到改革开放,人们才重新获得自主经营的权利。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经济好了,是因为政策好。但“政策好”是指什么呢?就是让人们放开手脚去做事。国家不需要刻意地去推动什么,市场自然就会繁荣。而国家过度介入的时候,经济便受到损害。
03 微观史叙事是历史写作,而非文学想象
界面文化:两年前《袍哥》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和公众对微观史的关注,据你的观察,目前国内对微观史的态度是怎样的?
王笛: 现在国内流行的微观史作品主要还是从西方译介过来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大家的阅读兴趣,受到了重视,但是真正把微观史作为实践来写的还非常少。因为它面临很多问题,最困难的是资料问题。微观史一般研究身处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话语权,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少,研究起来就很容易受限。
另外,《袍哥》的出版也让我发现,大众读者对微观史还是缺乏认识,不太了解微观史写作的难度在哪儿、意义在哪儿。过去的历史书写只把眼睛对准帝王将相,民众作为历史的大部分反而被忽略了。《袍哥》受到历史学界乃至文学界的重视,说明这个视角转向受到肯定,但有的普通读者把它当小说来读,对其中的补充资料很不以为然。
举个例子,有读者评论说,我把一个2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当作基本资料,写了20万字,这是“注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恰恰是微观研究的魅力之处,从小处着眼,但是把眼界逐步扩大,涉及对资料的文本分析、事件发生地点的考证、彼时社会学概念的清理、当时田野考察方法的运用,甚至追溯到社会学和人类学进入中国这样的大背景。它是一个历史的写作,而非文学的想象,挖掘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意义。
微观史还在经历一个让大家逐渐熟悉的过程,我相信以后会逐步发展起来,我也会继续写下去。

成都街头的理发摊。来源:图虫
界面文化:你从早期宏观的、具有计量史学的历史研究转向偏于叙事的微观史研究,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还是对史学公共性的反思呢?
王笛: 首先是学术兴趣。过去我在国内主要研究经济史、政治史,在美国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不再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写作的方式也需要转变,为日常生活提供一种新的理解。
我在写作的时候也会考虑,怎样才能提高一般读者对专业历史著作的阅读兴趣。《跨出封闭的世界》是我的第一本书,里面两三百个统计表和大量的数据,一般读者谁读得下去呢?很多专业历史著作里面都会出现不少专业名词,大量直接引用史料,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自己先把原文史料消化了,经过思考加工,再把它用叙事的笔调讲出来,专业性的东西放到注释里面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看。
最后是对史学方法的探索。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几乎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历史学其实属于人文学,它不是社会科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运用大量的统计和分析,影响了历史的可读性。中国过去的传统也是文史不分家,读司马迁的《史记》就能感受到文学的色彩。目前我在方法上综合了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一种多学科交叉的探索。这几个因素造成了我现在写作的一些特点。
界面文化:你认为文学性的语言、文学想象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
王笛: 在《显微镜下的成都》里面,“茶馆”一章收录了我对1900年1月1日的“早茶”和1949年12月31日“寻梦”两个场景的描写。这两个场景的描写非常细节化,带有文学性,但文学的笔法在这里只是一种手段,实际上我所写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资料作为依据的,而不是凭空想象。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读者邀请到我所写的场景中来,像电影一样,融入到那个茶馆的气氛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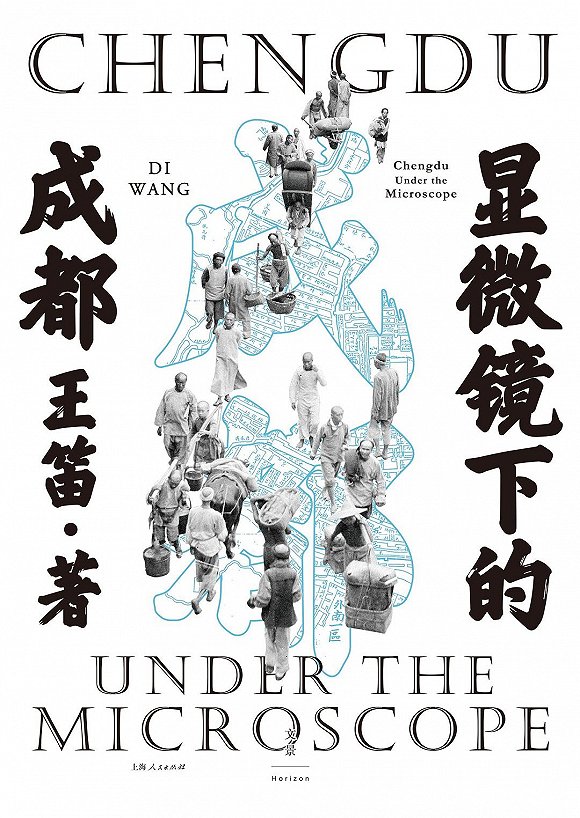
《显微镜下的成都》
王笛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7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