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里,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Snapchat短片捕捉着我们一天天的生活,Instagram用户们精心策划着他们的个人主页和短视频,事无巨细的Twitter帖子讲述着早间通勤路上发生的一切。我们每个人都是讲故事的人、旁白、故事的传播者。多数故事是我们自己的,当然偶尔也有其他人的故事。我们都坚信,任何人都有故事,我们需要的只是把它们讲出来的勇气和空间。但在现在,仅仅有某种经验已经不够,把这种经验分享出来也无法让人满足。人们感觉有必要插上一面旗子,申明故事的所有权:“这个故事属于我!”出于本能,有人认为自己的经历总是比其他人的经历更重要,认为自己的经历永远是“具有原创性的”。
当故事根植于创伤时,各种与道德相关的问题便随之浮现。我们该如何讲述涉及这种经历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讲出来?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受众在未来对于此类故事的接受度?在这个注重原创性的时代里,最重要的问题恐怕还是:谁有资格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据称,凯特·伊丽莎白·拉塞(Kate Elizabeth Russell)的处女作《我的黑蛱蝶》( My Dark Vanessa )给她带来了上百万英镑的预付款收入,这部作品是2020年宣传声势最大的一本书(这两点不无联系)。这本小说中的故事始于2017年反性骚扰运动的高潮,主人公瓦内萨在那时发现她在高中时代交往过的英语老师被一位曾经的学生提起了性侵指控。这项指控使得她重新考量了她和这位老师曾经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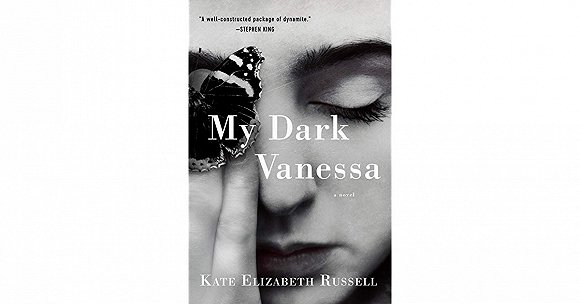
《我的黑蛱蝶》
今年1月,美国出版商Flatiron取消了《美国污垢》( American Dirt )作者让尼娜·卡明斯(Jeanine Cummins)在美国的巡回签售活动,原因是作者和出版商因为书中对于墨西哥移民的描写而受到了威胁。这本书也同样被认为宣传过度,且背后涉及一桩高额交易。在此之后不久,《拉丁裔美国人》( Latinx )作者温迪·C·奥尔蒂斯(Wendy C Ortiz)指出,《我的黑蛱蝶》的情节和营销方式和其2014年的回忆录《挖掘往事》( Excavation )“惊人”相似,这本书讲述的正是她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和一名英语教师的性经历。Twitter上的键盘侠因此火力全开,指控拉塞抄袭,并称她是又一个利用边缘群体经历牟利的白人作家。在今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奥尔蒂斯称,拉塞表示自己在撰写《我的黑蛱蝶》的20年间读过《挖掘往事》——作为其素材之一。
温迪·C·奥尔蒂斯非常克制地质疑了拉塞撰写关于性虐待小说的动机,以及后者为何要“通过阅读与该主题相关的书籍”来撰写作品。奥尔蒂斯用到了“小说化”和“大肆渲染”这样的字眼,这样的字眼引人注意,因为它们似乎是在暗示拉塞这样的白人女性无法体验那种创伤,而且写这样一部小说,也并不是一种讲述这种经历的合适方式。
当人们开始要求拉塞证明自己有过小说中那样的亲身经历时,她表示,《我的黑蛱蝶》的确是基于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写出的(很难想象如果举证,证据中会包含怎样的内容)。她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写道,“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强迫受害者向公众分享其个人创伤中的细节。”她还称,她害怕“进一步公开过去会导致二次伤害”。
这正是此问题的难点所在。人们现在觉得自己可以决定小说作者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这一点糟糕透顶。但这次的争议把另一种令人担忧的想法摆在了大家眼前:你必须经历过某种创伤,然后你才能写它。而且,描写这种创伤的方式只有一种,即通过自传。一个人可能会选择在虚构作品提供的保护之下道出自己的经历,这件事有那么不可思议吗?
让人与创伤经历保持距离也好,防止亲朋好友产生过度反应(作者或许不想向自己的某些朋友和家人透露相关经历)也好,虚构作品向作者提供了探索和解决敏感、复杂议题的空间。我们真的要强行替别人决定它们该怎样描写这样的经历吗?
雄心勃勃的小说家常常被要求“写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这种要求常常被误解。女性作家的首部作品常常被当成几乎完全基于自身经历、少有改编的自传,这种认知由来已久。我自己的首部作品讲述了一名年轻女性不为人所知的创伤,这部作品也被如此看待。公众、评论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虚构作品的作者一定经历过了他们作品中描述的创伤,但让小说作家证明这一点的要求还前所未见,这种要求非常令人警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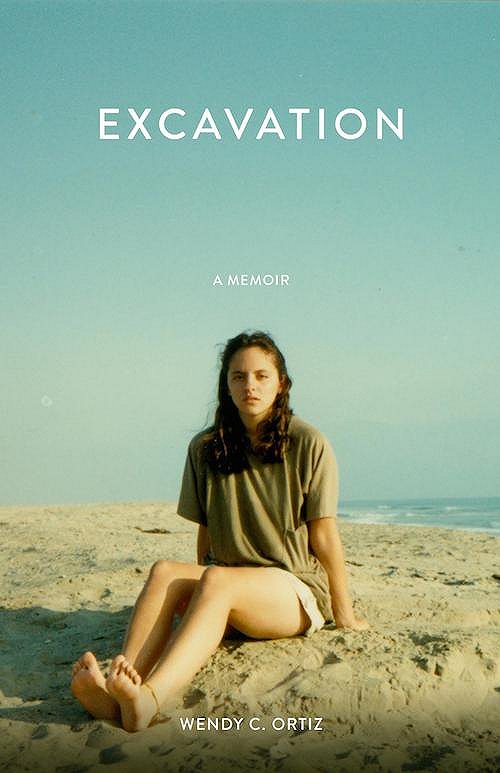
《挖掘往事》
不管温迪·C·奥尔蒂斯是否认为凯特·伊丽莎白·拉塞表示其作品基于真实经历这件事,和她承认自己读过《挖掘往事》这件事一样“来得有点太晚”,我能理解奥尔蒂斯说她对描述个人经历的虚构内容毫无兴趣时所表现出的愤懑。这又要回溯到对于一段体验的所有权的问题,它涉及到关于表现创伤的道德问题的核心。如果你有过某种可怕的经历,那么他人试图通过这段经历进行艺术创作的企图,可能会显得非常有侵犯性。它伤害了你的经历的独特性,当你觉得你的故事被忽略时尤其如此。
另一个维度的问题是,我们看小说、看电影、欣赏艺术,因为我们希望从中收获快乐。如果这种快乐是建立在某人的真实痛苦之上,一种令人不适的紧张感便会随之而来。问题在于,这条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定?是不是只有经历过战争才能描写战争呢?那么癌症、瘾症、精神问题、家庭暴力呢?是不是非得拿出本人经历过这些创伤的证据,然后才能基于它创作虚构作品呢?
过去几年里,文学界兴起了一阵#OwnVoices(我们自己的声音)运动( #OwnVoices运动提倡有少数族群身份的人物应当由来自少数族群的作者创作——译注 )的热潮,旨在放大边缘作者的声音,这是很有必要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被与#OwnVoices运动的观点混为一谈,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且这个论点也不是关于角色或著作内容本身的。承担写实功能的是生命书写(life writing, *涵盖当代个人书写的多变形式,包括访谈、民族志、个案研究、日记、网页等等——译注* ),我们不能允许自己把审查小说家当作常态。
关于这些争议,有一个更宽泛的议题不容忽视。温迪·C·奥尔蒂斯在她的文章中着重指出,出版业中白人占压倒性多数,英国89%、美国76%的从业者为白人。这种情况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整个行业对白人读者有种倾向性。编辑告诉奥尔蒂斯,要把她的作品《挖掘往事》推向较广的读者群体很难。这样看来她的理解没错,因为更广的读者群体正是白人群体。市场导向如此,出版商们会拿这样两个问题拷问自己:读者期望从拉美裔、阿拉伯裔、非裔(或其他少数族裔的人)的书中读到什么?这本书是否符合了读者们的预期?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出版商很有可能不会冒险出版它,更别说支付七位数的预付款并为之大肆做宣传了。与其问为什么有人会写一本关于性虐待的书,不如问,为什么整个行业都认为一本由拉美裔作者撰写的同一议题的作品卖不掉呢?出版商们认为读者从这样一本回忆录中期待看到什么?为什么出版商们不愿意挑战那些假设?
如果这个行业更加多元,审稿编辑应当能够指出,文本中的西班牙语不符合故事设定的背景,封面设计师应当不会轻易被充满刻板印象的装饰图案吸引,策划编辑或营销人员应当深耕边缘文化和艺术市场。一个更加包容的行业会来带更加多元的书籍,这些书籍应当能够迎合口味更独特、更多元的受众。出版商应当愿意把筹码押在更具有冒险性的书上。在整个行业真正不再把实现多元化当成做表面文章之前,我们恐怕还会看到很多关于谁有资格该写什么,以及关于如何写作的争议。
本文作者Layla AlAmmar是一位作家,著有《我们的约定》(The Pact We Made)。
(翻译:王宁远)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