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民粹主义的发展找一个起点,把东堪萨斯州作为其摇篮,可以说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了——这里是不折不扣的美国地理中心。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干旱横行,农场主联盟(Farmers'Alliance)等一系列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根发芽,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府愿景:“农民的权益高于银行家、企业家和铁路等基础建设。”在温菲尔德,一份激进的报纸《美国非圣公会人民与堪萨斯工业解放者》(American Nonconformist and Kansas Industrial Liberator)首次将“民粹主义者”(populist)这个概念呈现在铅字上。当时的“民粹主义”意指1891年创立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提出的劳资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分级所得税以及其他以人为本的政策的种种主张。非圣公会教徒在民粹主义阵营坚定地高举大旗,但就在北边两百来公里外,堪萨斯的主流共和党媒体则大肆嘲弄这些改革派,说他们是一群满腹牢骚的乡巴佬。
130年后,在特朗普入主白宫、脱欧一地鸡毛、博尔索纳罗统治巴西的今天,民粹主义与反民粹主义两种观点都活跃在舆论场上,而且应用容易定义难的问题多年来依旧存在。
“打从诞生之日起,民粹主义就有两重含义。”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人民?不:反民粹主义简史》( The People, No: A Brief History of Anti-Populism )中写道。这本作品简洁明快,令人大开眼界。“在支持者眼中,民粹主义意味着普通市民对民主经济改革的诉求。而反方辩手则认为,民粹主义源于空穴来风的不满情绪,领导者极富煽动性,带领一帮乌合之众掀起一股危险的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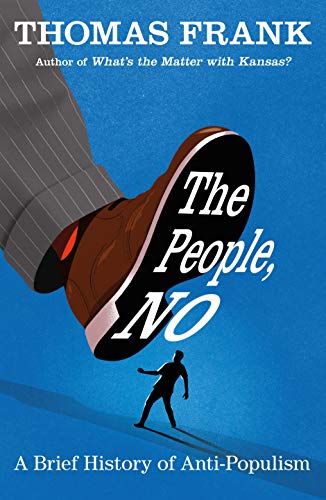
《人民?不:反民粹主义简史》
托马斯·弗兰克是原《哈泼斯》杂志的专栏作家以及《异见者》(TheBaffler)杂志的元老编辑,他的作品《堪萨斯怎么了?:保守派如何赢下了美国心脏》(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 )畅销美国。弗兰克可以说是讨论这种民粹主义二元性的绝佳人选了。从1891年始,到近年来特朗普主义的崛起,这位作者带着读者穿越一片雷区,甄别种种关于民粹主义本质与历史的推论和设想。他反思了1896年美国总统选举,也由此奠定了本书的节奏和基调。在这场选举中,民粹主义者与民主党人之间建立起新联盟,前者的支持帮助民主党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获得了提名。另一边,共和党则与大财团联手,推动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走上总统之位,也让民粹主义的衰落雪上加霜。
弗兰克强调,民粹主义植根于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等美国国父的平等主义思想中,抨击现代民主党和共和党精英对劳苦大众轻蔑的态度。他认为,这种看法“和维多利亚时代、大萧条时期一样,都是毒害社会的”。他有力指出,电视节目总是将民粹主义的标签从马丁·路德·金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身上撕下来,而仅仅将其附着于仇外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特朗普的推特咆哮之上。他认为,民粹主义一经掉价,美国民众就抛弃了其中有机的政治价值,背离了原本孕育了劳工和民权运动以及几十年持续繁荣的沃土。到头来,人们的选择就只剩下两极分化的华府精英体制和专制特朗普主义。
《人们?不》的中间几章阐释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这一政策融合了民粹主义与精明的自由主义,帮助数百万人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度过一劫。尽管如此,他的新政却为自己树敌无数——包括共和党人、其背后的华尔街撑腰者,以及许多美国大都市的新闻媒体。弗兰克在书中讲述了杜邦家族与其他富有的实业家如何或是牵头建立,或是慷慨资助各种右翼自由主义组织,以求推倒罗斯福,将他贬为社会主义者、自己阶级的叛徒。
罗斯福继第一任期的一系列新政项目后,在1936年再次获得民主党提名时火力全开,对保守派政敌发出了强烈抨击。“这些经济上的‘保皇派’声称我们在颠覆美国的体制,”他的话语如雷贯耳,“实际上他们真正不满的,是我们要收走他们的权力。正因为我们忠于美国体制,才必须剥除这种权力。保守派想要躲在国旗和宪法之后,可惜这是徒劳的。他们只不过躲在自己的盲目之中,以至于忘记了国旗和宪法的真正意义。”
在弗兰克看来,十九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运动和罗斯福新政中的自由主义有着清晰的关联。他认为,正是因为他一反同代人的作风,拒绝入伙商业金融精英,而寻求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和法兰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等人的支持——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改革者,能够意识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的使命不是强化现有制度,而是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全新的严峻挑战。

富兰克林·罗斯福
“虽然放在今天来看,自由主义者要想认识到这一点,或许会经过一次阵痛,但正因为罗斯福将精英拉下高台,才最终赢得了抵御大萧条的胜利,”弗兰克总结说,“如果说当时的这些英雄都是怪人的话,那么感谢上帝让美国拥有这些怪人。感谢上帝,让民粹主义诞生。”回看今天这一历史时刻,乔·拜登也应该以史为鉴,从中学习。
二战后,反民粹主义兴起,而美国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则成为了弗兰克批评的靶子。他在1955年的代表作《改革的年代》中赞扬了专业、多元、仁义且有行政管理能力的资本主义,同时将人民党视作低智商的种族主义者和麦卡锡主义的忠实拥趸。
“换句话说,”弗兰克批评霍夫施塔特,他认为“当改革自下而上发起时,就是说教的、蛊惑人心的、不理性的、偏执而徒劳的。而如果由现实的商业专家——也就是说客和与之为伍的专家——来进行的话,繁荣就不是难事”。
从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到民权斗士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从民主党参议员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到导演弗兰克·卡普拉甚至是查尔斯·科格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从共和党总统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到极右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人民?不》这本书中,弗兰克通篇都在尽力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视角来阐释民粹主义。他恰如其分地讲述了身穿牛仔裤的吉米·卡特如何用民粹主义来包裹自己,以免被贴上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是保守派的标签。在弗兰克看来,卡特是一个“无聊的技术官僚”,披上民粹主义的外衣赢下了白宫,却选择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来担任自己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曾有一句名言:“美国民众的平均生活标准必须降低。”他以20%以上的利率达成了这一目的。
弗兰克还批评了比尔·克林顿、罗纳德·里根、巴拉克·奥巴马和所谓的“蓝领百万富翁”特朗普,怒斥他们与华尔街精英、领导阶级为伍,是民粹主义赝品。奥巴马曾将民粹主义大军看作反科学、沉迷枪支和宗教的狂热分子。奥巴马在2016年还批评一位候选人,“投降残暴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者鼓吹回到过去,但是回到过去哪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希拉里·克林顿也难逃一劫,因为她将特朗普的支持者塑造成“可悲的、无可救药的人”。
在《人民?不》的结尾,读者可以清楚看到弗兰克的立场了。面对那些害怕“下层社会”利用权力碾碎和平运动、罢工游行和疾呼全民医保的精英,他怒不可遏。他认为,像民主党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这样的政客应该更多一些。
“美国的立足点在哪里?”他在结尾抛出这样的问题,“百万富翁?名人?还是科技公司?民众只不过是为了发薪日改善生活而辛苦劳作、愤愤不平的工具吗?我们是戴着勋章的卫兵,忠诚地保护资本家的财产吗?我们是否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测验田,时刻可追踪可调查,被兜售各种票券、快餐、充斥着层出不穷的特效技术的好莱坞电影?亦或许恰恰相反,该接受服务的其实是我们?”
弗兰克希望读者好好思考这个基本问题,并且了解到,民粹主义的本质只有一句话:这片土地是为你我凡人而造的。
本文作者Douglas Brinkley系莱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CBS新闻的历史专家,以及《名利场》的特约编辑。
(翻译:马昕)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