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当《时代》杂志的封面选中科尔森·怀特黑德时,称他为“美国故事讲述者”。这不仅是对他2016年小说《地下铁道》取得的非凡成功(该书同时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的认可,更是对他更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的认可。
与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一样,《地下铁道》是一部跨越岁月的历史小说作品,它有力地唤起人们的共鸣,揭示了美国当代不满情绪的根源。去年,怀特黑德又推出了《尼克男孩》,即将在英国出版平装本。这部作品比前作更精简、字数更少,而且以近代为背景。它巩固了怀特黑德的文学地位,并在上个月为他赢得了第二个普利策奖。
这是他与少数人分享的荣誉,其他二度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纳和约翰·厄普代克。“美国故事讲述者”这个描述突然间显得更加贴切。我问他是如何处理所有这些赞誉和它所带来的期望的,“这一切都很抽象,”他回答说,“我仍然能够体会到巨大的忧郁,然后当我想到我的第二个普利策奖时,这既让我疯狂,也让我非常高兴。我想我还没有真正接受它进入我的世界,所以它仍然与我保持着距离,但同时又非常可爱。”
我电话采访了怀特黑德。他和妻子朱莉·巴勒(文学经纪人)以及孩子们——15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一起安居在长岛东汉普顿的第二个家中。

《尼克男孩》
“我已经居家隔离12周了,”他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最初的几周是最糟糕的。然后你会在一定程度上习惯,并做出调整。但我们在这里12周了,还在摸索新的现实。一切仍然是相当不确定的。”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隔离的不确定性已经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谋杀乔治·弗洛伊德后爆发的抗议活动所打破。与一个近作皆在探索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及其阴影的小说家在当下聊天,是一件有趣的事。
“好吧,如果你选择写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我们的邪恶能力,”他说,“可以写1850年、1963年或2020年,不幸的是,这一切在这些年代里都适用。不仅现在正在发生,而且会持续很多年。”他听起来对改变并不乐观。“过去几年在写种族问题的时候,我也一直生活在关于警察暴力的时不时的讨论中。这类讨论从非常响亮又变得安静,当一件事情发生时又再度响亮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贯穿着我的生活, 但在过去几年尤甚。所以,仅仅就个人而言,它变得如此直接,并且看到它现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孩子们的生活,已经让我精疲力尽。”
重读他最近的两部小说,叫人很难不把警察杀戮视为某个连续事件的一部分,嵌入并经常暴力地表达种族不公正,比任何其他单一问题都更能定义美国。萨拉·柯林斯(Sara Collions)在为《尼克男孩》英国平装版写的序言中指出——序言是她在过去几个月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写的——“这不仅仅是一堂历史课,尤其是当我们还得宣称黑人的生命很重要的时候,当埃尔伍德和特纳的角色更有可能让我们想起特拉伊冯·马丁)而不是哈克贝里·费恩的时候。”
2011年,特拉伊冯·马丁只有17岁,他在去姐姐家做客时,被一名白人邻居开枪打死,这名安全志愿者认为马丁的存在很可疑,甚至带有威胁。杀害他的凶手后来以自卫为由被判二级谋杀罪不成立。从那时起,在种族仍然是决定性因素、美国政治文化日益撕裂的背景下,被白人执法者杀害的黑人公民数量成倍增加。怀特黑德是否认为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可能是第一个迹象——不仅仅表明人们已经受够了,而且真正的改变即将到来?

2017年,科尔森·怀特黑德与妻子朱莉·巴勒在纽约 图片来源:Patrick McMullan/Getty Images。Patrick McMullan/Getty Images
“过去的五天(我们在第一波抗议活动后进行这次对话),就抗议活动的范围和规模而言,是相当不寻常的,”他说,“就像有人在网上说的那样,‘美国50个州上一次在某件事上达成一致是什么时候?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先兆。而且一般来说,年轻人抛弃掉父母那一代人说的话和做的事是件好事。我们已经做得够遭了,所以越不听我们的话越好。但是,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到底能带来什么。希望它能在11月的选举中转化为一个比四年前更好的结果。”
我说,这听起来像是他刻意让自己保持乐观。他凄然一笑,“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乐观。想到唐纳德·特朗普会在11月再次当选,我可能会疯掉。所以,为了我自己的理智和孩子们的未来,我必须认为这不会发生。人们想谨慎乐观地认为这些抗议活动会让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但也可能不会。”
他停顿了一下,组织自己的想法。“在特朗普的统治下,任何一种体面的形式都被撕得粉碎,我认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试图找回理智。希望我们能集体做到这一点,但共和党人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来尽情释放他们的破坏力——甚至可能是四年零六个月。他们还没有下台。另外,特朗普是个疯子,谁知道他会想做什么?他甚至可以拒绝卸任。”
与前作一样,《尼克男孩》也是一部基于事实的小说,内容是幸存者对佛罗里达州杜泽尔男校生活的描述。该学校成立于1900年,2011年因被指控长期虐待——包括实施酷刑和谋杀——而关闭。2012年,当地的法医调查发现了55座无名墓。“这是一个故事,”怀特黑德说,“关于有权势的人如何虐待无权势的人,却从未被要求承担责任。”
叙事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南方民权抗议活动背景下展开的,而这些抗议活动对于两位主人公埃尔伍德和特纳来说再遥远不过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剥夺了自由和希望。就像《地下铁道》中被无情的捕奴人里奇韦追杀的逃亡奴隶科拉一样,他们的生活也被国家认可的结构性暴力体系所定义,这种暴力体系是无所不在,是常态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享有特权的白人多数派的合谋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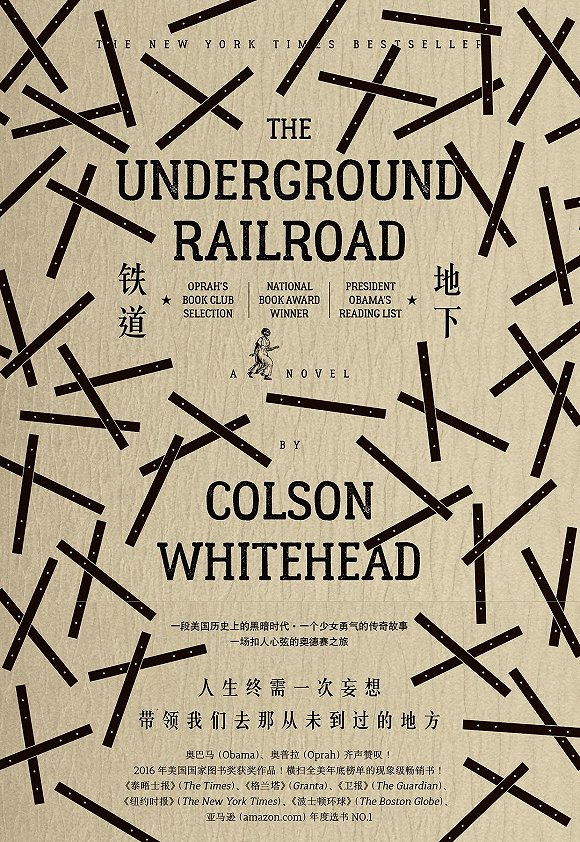
《地下铁道》
[美]科尔森·怀特黑德 著 康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3
“杜泽尔男校有实际的施虐者,”怀特黑德继续说,“但也有一个所有处于权力地位的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体系。佛罗里达州政府没有跟进调查,他们没有解雇腐败的主管或主任。相反,这些人继续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哪怕有人被杀害或失踪。”
这与当代美国治理之间的相似之处很有说服力,无论如何,我们似乎正在特朗普的带领下倒退。“现在有警察杀人事件,有一个完全荒谬无耻的领导人,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身处的荒谬与可怕之中。现在有大流行病正在蔓延,和平抗议被用军事力量镇压,前所未有的腐败在幕后进行,这一切都在当下可怕的汇合中同时发生,我们都是它的见证者。”
怀特黑德从小在曼哈顿上东区长大,他当时的名字是阿奇·科尔森·奇普·怀特黑德。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都是成功的专业人士,经营着一家高管招聘公司,并将孩子送进了私立学校。怀特黑德形容他2009年的小说《萨格港》比自己的其他作品更谦虚和个人化:“小学要求我们穿夹克、打领带,我们照做......我们每人有一件蓝色西装外套和一件米色灯芯绒外套,轮流与灰色休闲裤和卡其裤搭配。”
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和弟弟在人行道上被一个好奇的白人老者拦住,他询问道:“你们是不是外交官的儿子?是不是某个非洲国家的小王子?”因为联合国总部就在半英里之外,不然黑人为什么会穿成这样?
他从小就是一个贪婪的读者,读的大多是漫画、科幻小说和悬疑小说:罗德·瑟林、厄休拉·勒古恩、斯坦·李、斯蒂芬·金。怀特黑德在2012年为《纽约客》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将年轻时的自己描述为“有点闭门造车”,当别的孩子在中央公园玩耍时,他“更喜欢躺在客厅的地毯上看恐怖片”。
六年后,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他从更鲜明的角度回忆了自己的孤独。他解释说,他和弟弟(2018年去世)会沉浸在漫画、电子游戏和幻想小说中,以逃避父亲酗酒导致的情绪波动。“我父亲爱喝酒,有脾气,”他说,“他的性格就像是家里的天气。”怀特黑德还形容他的父亲“对美国的种族主义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世界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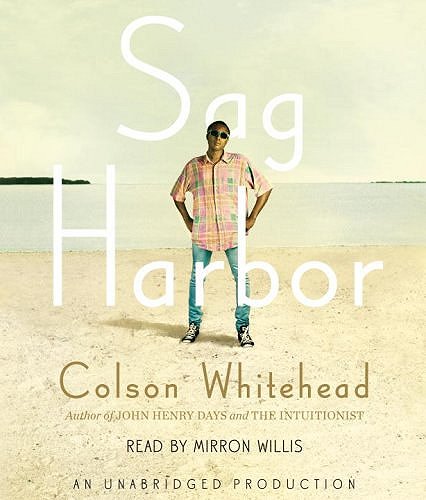
《萨格港》
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我能感觉到怀特黑德继承了他父亲的悲观主义。“我想相信事情会发生变化,但后来发生的可怕事情让我觉得并非如此。他有一次告诉我:‘但是,你必须保持希望,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否则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尽管他的背景相对比较受宠溺——私立学校,夏天在汉普顿的萨格港度过——但怀特黑德也不可避免地亲身经历了美国随意的种族主义治安,却把它当作几乎不值得谈论的事情。“这总是存在的,”他疲惫地说道,“就拿被警察抓这件事来说,每个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已经到了没意思的地步。这是我十几岁时就熟悉的白人执法方式,这是我父母的经历,也是我祖父母的经历。”
这种可能性是否让他怀疑小说是否真的能改变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政客不读书。”不过,奥巴马是个公认的例外,他热情地推荐了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就立法而言,被艺术打动然后进一步去制定一些法律的人,通常不是读书或听音乐的人。从个人层面来说,艺术能提升、滋养、激活人生;但就立法而言,小说在美国的文化中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中心地位了。”
少年时代,怀特黑德听的是后朋克和新浪潮音乐。“我记得我姐姐回家后会开始放Gang of Four和Liquid Liquid的音乐,1978到1984年的全部后朋克浪潮的乐队,我听到了这些。当我开始去CBGB和Irving Plaza俱乐部时,我看到了Sonic Youth、The Fall、Butthole Surfers和Big Black乐队的表演。”

Sonic Youth
他说他现在还在听那个时代的音乐,事实上,就在我给他打电话之前,他还在听。他的女儿最近在Spotify上发现了The Cure。“这有点奇怪,”他笑着说,“不过,嘿,希望新浪潮永远不会消失。如果50年后人们还在玩糟糕的合成器流行音乐,那就太好了。”
怀特黑德刚完成了一本新书,他把这本书描述为一部以哈林区为背景的犯罪小说。这就是他愿意透露的全部内容。他告诉我,如果他“能在五天写出不错的八页内容,就足够好了”。被隔离是否影响了这种规律,甚至给他提供了更多的写作时间?“嗯,前六周我根本没有写作任何东西,只想确保孩子们没事,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好。然后,我想也许我可以每天工作一两个小时,要想重新进入状态真的很难,但书是不会自己写完的。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被瘟疫或闪电击倒了怎么办?我更愿意先把书写完,而不是不写。”
2011年,在出版了四部截然不同的小说,包括广受好评的处女作《直觉主义者》(
The Intuitionists
)后,怀特黑德还写了一本关于流行病的小说,《第一区》(Zone One
)。这本书的背景是,在饱受摧残的后世界末日的美国,一种传染性病毒将人类变成了食肉僵尸,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努力重建。
我问,如果他当时知道了现在知道的事情,会不会写出一本很不一样的书?他为这个想法笑得合不拢嘴。“好吧,借用几个月前在推特上流传的一个笑话——我真的没有意识到在世界末日时卫生纸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一定会写得更平凡、更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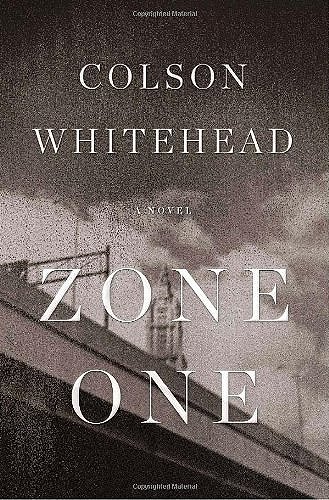
《第一区》
“在对流行病的巨大恐惧下,会发生很多荒唐小事——人们在杂货店里为争夺物资而争吵,地铁司机不得不吸入乘客呼出的空气,这就是瘟疫小说的内容。还有一种反常的做法,就是当着别人的面咳嗽来嘲笑他们,因为他们戴着口罩而你没有,”他叹了口气,“这些不合理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你真的想不出来。人性的怪异超越了你的想象。”
他不止一次地使用了“人性”这个词,让人感觉他过去几本书的写作强化了他的基本信念,正如他曾经说过,“人是可怕的——我们发明了各种不同的理由来恨别人,一直如此,而且永远如此。”他真的这么认为吗?“嗯,就人性而言,强者往往会暴虐和欺凌弱者。我真的不认为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将继续以我在《尼克男孩》中所描述的方式那样,以相当可怕的方式互相对待,直到永远。”
就这一切而言,《尼克男孩》中尽管有一些黑暗的、近乎哥特式的恐怖段落,但它是一部有救赎意味的小说,一个幸存者的故事。我想知道,在他最近的小说中,对创伤人物的写作以及对他们生活的追溯,是否对自己造成了心理伤害。
“在写《尼克男孩》的最后两周,我感到非常疲惫和沮丧,这对我来说很新鲜。《地下铁道》也写得很艰难,但它对我的影响不一样。我对埃尔伍德和特纳这两个角色很有感情。两年前,我就有了让他们走上正轨的想法,现在却要结束了。我记得,当我在2018年7月4日那个周末完成这本书时,我只是关掉了Word,打开了XCOM,玩了六个星期的电子游戏,而且我开始吃素。”
他告诉我,在整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每天早上都会打开电脑上的一个文件,看到他开始写作时写的一句话。上面写着: “有罪的人逃脱了惩罚, 无辜的人在受苦。”他写这句话是为了提醒他所讲的故事到底是关于什么的。“然而,”他说,“这本书的最后三分之一,其实说的是所有没在这两行字里的东西:怎么处理这种问题?你如何用这样的知识生活?还有,你如何创造生活?”
正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科尔森·怀特黑德成为了美国在这个动荡不安时代里的故事讲述者。
本文作者Sean O'Hagan是《卫报》特约记者。
(翻译:李思璟)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