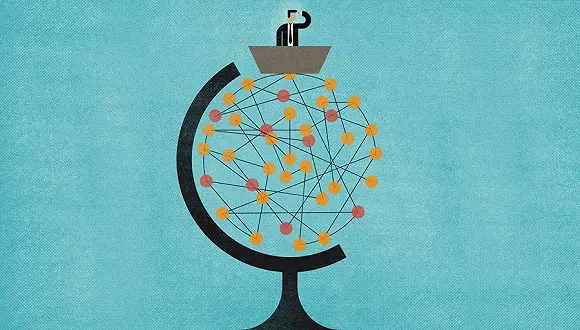当今世界由近200个国家组成,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哪怕他可能不认同自己的国家——这似乎是个常识,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很多国家甚至谈不上是“国家”。因为在社会学理论中,现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其实是现代化的特殊产物,一如理查德·拉克曼在《国家与权力》中着重强调的,它并非自然产物,也不是“不可或缺、静止不变的组织”,而是特定历史条件催生的,进而在征税、征募公民建设常备军、建立民族认同、建构民族文化这四个领域都扩展权力,最终在国境之内垄断了征税、暴力与合法性。
这乍看很平常,因为现代国家无不如此,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做不到——至少是那些所谓“弱国家”或“失败国家”。像索马里之所以还被世人看作是一个国家,仅仅是因为它在世界地图上被涂抹为同一种颜色,但在现实中,它陷入无政府状态已长达数十年。正因此,2004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一书,强调在第三世界,“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两年后,他又撰文《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一文,大体延续了《国家构建》的主旨,因为“美国所谓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就是国家构建,亦即构建政府机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强调这不仅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甚至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而言,都是最主要的挑战。
本书的英文名也是Nation Building,所强调的重点也很近似。在英语中,state和nation都包含有“国家”的意味,但前者更偏向“政府”意味,强调作为一个政治权力组织的“国家”,而后者则侧重“国族”,突出“国家”是由全体民众构成的共同体。不难想见,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虽然也需要制度性的国家力量参与,但重心却落在如何促进内部的有机团结上,最终“合众为一”,创造出国民的凝聚力。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锻造,并不仅仅是“失败国家”的问题,而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面临的现实,在欧洲尤其如此,像西班牙反倒是经济最发达的加泰隆尼亚地区的国家认同最低。
国家认同来自政治代表性
由一个瑞士学者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再合适不过了。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多元族群共和国之一,瑞士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中立和平,内部虽然有分歧,但族群差异在政治舞台上并不重要。因而对于像欧内斯特·盖尔纳这样将一种单一的共同语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学者来说,瑞士代表着一项重大的干扰,是很难纳入理论框架的奇怪例外。但从现在欧盟作为一个多元整体的角度来看,瑞士却是一个典范性的先驱。看看各地比比皆是的失败案例就不难发现,这并不容易做到,需要长期缓慢的政治生态演进,并取决于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整合是否成功。
这其中一个两难的困境在于:“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整合”本身需要以现代公民身份为基础,使得人们不再将自己首先看作是某个行会、城市、村庄、部落或族群的成员,而是看作与其它成员在基本权利上没有差别的公民,但恰恰这一点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个人从那种原生的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而这无一例外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在这方面,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更容易达成,因为很多人来到美国原本就是打算抛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开始新生活,追求“美国梦”,加上美国各州从不以语言为原则来成立,因而在美国虽然也有不同族群的组织,却从未出现族群语言来动员的大众运动,真正折磨它的是历史遗留的种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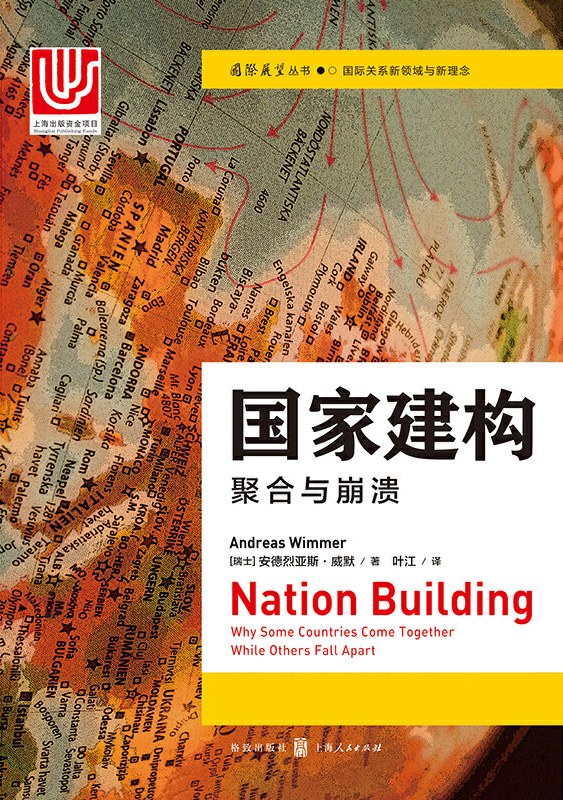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 著 叶江 译
格致出版社 2019年10月
棘手的是,在很多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动,反倒加剧了族群冲突,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就曾断言:“低度发展国家里的集体自我形象压倒性地是原生的(即部落、族群、地方的)或宗教的,断非公民的。由于每个集群的成员都倾向于相信,别的每个集群的成员只会为了自身集群的利益而行动,他们不相信充塞着这种人的那些公共机构绝不会损害他们。”这本身就要求公共机构保持中立性,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政治的思维是呼吁“天下为公”,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权威应当秉持公心,不偏不私;在西方,虽然目的类似,但方法却大有不同,强调在权力机构中拥有代表性,使自己的利益和声音得到表达和倾听,用书中的话说,“对国家的认同来自政治代表性”。但殊途同归,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要让人产生认同,让他们真切感受到“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那国家就得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并公平地进行分配。就此而言,那些“失败国家”要么是国家没有这样的能力,要么是在分配时将公共物品当作是自己所属小群体的肥肉,最糟糕的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现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新兴的国家力量试图强行推进整齐划一的国族身份,剥夺并整合地方精英的权力,鼓励他们采用主导群体的语言,但这样的努力有时却适得其反。拿破仑帝国占领整个比利时之后,法语被视为开明和进步的语言,而佛兰芒语则与非理性、落后、保守联系在一起,人们必须彻底掌握法语,才能有自己的事业。类似的情形在法国、爱尔兰、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印尼等各国不断上演,但结果是反倒沿着语言边界产生了对抗性的族群动员。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就很难出现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联合,像阿富汗、伊拉克和波黑的例子证明,即便是外部力量来推动整合,培育政治凝聚力,但最终也还是会归于失败。
如何达成权力的公平分配,这往往取决于精英斗争的结果。在瑞士,族群性从未被问题化、政治化,因为大众的政治动员是通过教会、行会等跨族群的社会网络进行的。换言之,这需要有发达的社会组织,使人们在争取自身利益时,并不首先自视为某一民族的成员,而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钟表制造商、教师或医生,族群身份因而无关紧要——如果有,也只认同“我们都是瑞士人”。1870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当时的首相阿泽利奥说:“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也暗含着这一层意味:全新而一致的公民身份必须取代原有的地方认同。
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其实往往是在一个分裂性结构的社会中维持内部凝聚力、进而争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这恐怕正是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很难找到其它可替代的机制来维护自己利益。但到了现代社会,就必须有一个容纳人们利益诉求的政治框架,因为国家认同说到底是权力与政治的问题,取决于人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对待,也只有当社会进一步多元分化之后,族群身份才会渐渐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了。
不同的熔炉
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可以说是“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则各有各的不幸”。本书在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案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族国家认同并不是族群同质性的产物,而是由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提供产生的。这么说有些抽象,举个例子就能理解了:日本在世界各国中算是族群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长期自视为单一民族国家,但即便如此,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并予以公平分配,那么各地难免会产生抱怨和疏离——例如冲绳这样的边远地区发现学校和医院不如东京这样的发达城市,又或者东京的贫穷阶层愤怒于自己得不到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社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多元异质的,是一个伴随着大规模流动性的丰富生态,而要在其中培育主动的共同体意识,就得“不让一个人落下”,使每个成员都觉得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关照。这意味着有效、公平的公共物品供给,由此也能让政治精英扩大其在全国的政治联盟和支持网络。
但这首先就得建立起一套有执行力的政治机制,而像索马里这样的国家建构计划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们连这样的基本能力也缺失:它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无政府状态,几乎没有任何税收基础,也就谈不上去建设道路、学校、医院并提供安全、福利了。《破碎大地》一书在考察近年来几个中东国家的命运后发现,人为造就的国家比较脆弱,往往既缺乏国家能力,又在权力分配上容易陷入纷争,最终,危机并不是促成凝聚力,而是带来分裂和混乱。

《破碎大地:21世纪中东的六种人生》
[美] 斯科特·安德森 著 陆大鹏 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06
正因此,本书才强调,“没有这种常规的官僚机构能力,就很难提供安全保障、主持正义、发展基础设施和提高广大公民的经济福利。没有有效的和公平的公共物品供应,该政权就无法将其支持基础扩展到其狭隘的宗族圈子之外。”不过确切地说,现实中这个问题更为棘手。美国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它这些年来的政治却并不是走向整合,而是分裂,特朗普的上台依靠的就不是将支持基础扩展到共和党之外的群体,而是依靠对已有群体的深度动员,因为仅凭这一点就已可以获胜。更有甚者,像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计划乍看有益于所有人,但却仍然遭到了共和党人士的坚决抵制。
这表明,如果说“提供公共物品产生认同”,这首先需要产生一种意识,那就是将国家视为一种达致自己利益分配的机制,意味着国家被社会所捕获,成为表达社会利益的渠道;与此同时,还需要一个能促成妥协与整合的政治框架,使党派之间的恶斗不至于阻碍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另一个前提是国家垄断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而这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甚至直至今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非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仍是国家的竞争者,例如在地震中为灾民提供救济的日本黑社会组织。
以此反观中国,也会给我们以很大启发。正如福山近些年也注意到的,中国政治模式非常早熟,很早就建立起了强大的官僚机构,而至少精英阶层的国家认同也早就压倒了地方认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整合不是通过法律框架下的代议制,而是政治权威推行的“编户齐民”与“书同文”,即通过整齐划一的户籍和统一的书写文字,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上对国家有效而公平的分配与其说是一种权利,倒不如说是一种伦理期待,坚信国家应当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权威。
一直以来,中国人也期望国家能公平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甚至相信它“除了生孩子外无所不能”,但这种“国家强大”的期盼假设了全能的范围与全面的执行力,因而很多人不免困惑“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也有人这么贫困”——实际上,国家的强大只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维度,与一部分民众是否贫困其实是两回事,但中国人会发出这样的困惑,本身表明人们相信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应当从整体强大中获益的强烈愿望。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格外重视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人们发现自己不能平等地得到机会和好处时,就会产生不满和疏离。这是一种不同的“熔炉”,表明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机制来达成利益的表达、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公平分配,最终形成政治整合的共同体。不过,当社会逐渐现代化、根据经济学原理更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时,就会发现给予人们更有保障的权利,结合自由迁移,能更有效地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最大化地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这可能正是我们的未来。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