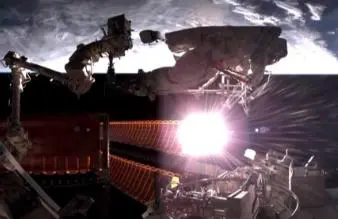新華社拉各斯6月1日電通訊:遺失在血色中的童年——生活在恐怖陰影下的尼日利亞兒童
新華社記者邵馨蓮
童年,本應是幸福與無憂無慮的代名詞。然而,在西非國家尼日利亞,因為宗教極端組織“博科聖地”的猖獗活動,不少孩子的童年被蒙上了一層血色陰影。
(小標題)“‘博科聖地’把我攆出了學校”
一個炎熱的下午,15歲的布拉瑪·布卡爾漫無目的地走在尼日利亞博爾諾州首府邁杜古裏的街頭,右臂上挂著一個骯髒的木盒。盒中既沒有教科書也沒有作業本,只有破舊的橡膠拖鞋、鞋刷和一些修鞋工具。
“是‘博科聖地’把我攆出了學校,”他一邊解釋為什么不去上學,一邊用右手抹去臉上的汗水。午後街頭近40攝氏度的高溫裏,他看上去疲憊極了。
布卡爾和家人原本住在博爾諾州南部。“2013年7月,我還在上初中,‘博科聖地’襲擊了我們鎮子,燒燬了我們的學校。夜裏,人們紛紛傳說,‘博科聖地’還會再回來,於是我父母和我逃離了村子。我就這樣來到了邁杜古裏。”
布卡爾一家就這樣開始了流落異鄉的生活。布卡爾說,他父母在熟人介紹下在邁杜古裏找到住處,他則在一個朋友那裏找到了落腳地,但必須自己養活自己,“於是我開始了修鞋的活計。”
帶著簡陋的工具,布卡爾每天走街串巷,大約能賺到6美元,“至少夠買吃的”。不過,他仍在懷念原本屬於他的校園生活。“我想念學校。修鞋不是一個孩子該幹的事。”他難過地說。
和布卡爾有著相似遭遇的孩子還有很多,沒能上完小學六年級的阿勃拉姆·道拉就是其中一個。
“博科聖地”曾在2013年連續三次襲擊道拉家居住的社區。“他們燒了我們的學校,殺了很多人,我父母不得不逃往喀麥隆。”道拉說。
11歲的道拉是家裏8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父母沒有帶他同去喀麥隆。他寄住在朋友家裏,在邁杜古裏一家餐廳洗盤子,每天能賺大約兩美元。
“‘博科聖地’毀了我想成為一名科學家的夢想,這是我最痛苦的事。”道拉說。現在,重返校園、坐在窗明几淨的教室裏讀書,只能出現在他的夢中。
(小標題)隕落的象牙塔
在尼日利亞北部的豪薩語中,“博科聖地”意為“西方教育的罪惡”。該組織成立於2004年,它的一個重要宗旨就是反對西方教育和文化,為此不惜對無辜的學校師生採取令人髮指的行動。
今年2月,在“博科聖地”的“大本營”博爾諾州鄰近的約貝州,“博科聖地”襲擊了一所大學,殺害了數十名大學生。4月,該組織在博爾諾州南部襲擊了一所女子初中,綁架了276名女孩。其後雖有一部分女孩逃脫,但仍有200多名女孩在“博科聖地”手中。“博科聖地”提出,要以這些女孩來交換遭尼日利亞政府關押的該組織成員。
恐怖活動對尼日利亞北部地區的正常教學已造成巨大影響。約貝州教育局長伊努瓦·庫柏告訴新華社記者,全州共有800多座校舍被“博科聖地”燒燬,政府正設法重建其中215座。州政府打算每月給北部學生的父母一些經濟補助,鼓勵他們繼續送孩子上學,但在安全威脅下,此舉收效有限。
對“博科聖地”的擔憂,甚至令一些學生不敢去上學。14歲的少女阿希拉是邁杜古裏一所私立學校的學生,但對“博科聖地”的恐懼對她造成了嚴重影響。阿希拉的父親艾哈邁德·傑洛說,阿希拉非常擔心學校會遭到“博科聖地”攻擊,“她不時告訴我們說,她不願去學校。事實上,我們也在不斷祈禱她平安。”
邁杜古裏大學副校長馬拉·道拉說,由於“博科聖地”3年多來的安全威脅,報考邁杜古裏大學的學生數量在逐年遞減。“今年,把邁杜古裏大學作為第一志願的考生只有2896名,而學校的計劃招生數為7000名。”
“博科聖地”給孩子帶來的不僅僅是學業的中斷,更有心理上的創傷。“一些孩子變得害怕與人交往。一些孩子害怕同樣的事(遭綁架)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甚至不願走出家門去上學。”尼日利亞記者道達·姆巴亞說。
他說,一些孩子的父母被“博科聖地”以殘忍的手段殺害,導致這些孩子出現行為異常。“這些孩子想要為父母報仇,他們會變得很容易被煽動,也會相對更容易參加一些極端組織。”
(小標題)從花季少年到亡命殺手
布卡爾們或許還是幸運的。他們只是背井離鄉,中斷了學業,而在博爾諾州、約貝州和阿達馬瓦州,不少與他們年齡相倣的孩子甚至被“博科聖地”招募“入伍”,成為襲擊和殺戮的製造者。
不少媒體報道指出,有時“博科聖地”發動襲擊是為了獲取給養,而從事這些搶劫活動的成員只是一些十幾歲的學齡少年。
在一些幫派文化盛行的社區,一些失學、無業的街頭不良少年極易被招募成為“博科聖地”成員。因此,儘管政府不斷開展清剿行動,“博科聖地”卻總是能不斷獲得“有生力量”,難以根除。
根據尼日利亞教育部公佈的數字,像這樣失學、無業的街頭少年在尼全國有數百萬之眾。
尼日利亞有識之士呼籲,政府應當採取措施,致力於解決北部的高失業率和高文盲率,並出臺具體政策,以消除類似“博科聖地”的極端組織滋生的土壤。(完)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