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和我准备交谈的几个小时前,美国大选的结果终于揭晓了。阿迪契是尼日利亚籍小说家,现居马里兰,但今年在拉各斯住了一段时间,她是在送女儿参加一场生日聚会回来的路上听到新闻的。“那是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她说,“每个人都在打电话:最好的朋友、妈妈、姐姐都打了电话来,我们都在电话里尖叫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医生,不久前刚刚返回美国。“他跟我都要疯了,”她说,“我都要哭出来了,因为我认为,这与每一个想要体面重归的人都有关。我觉得这真的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与渴望一些人道和人文的事物有关。这太令人感动了。”
和很多人一样,她的轻松心情,被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的强硬表现所带来的失望冲淡了。“我一直觉得,特朗普和奥巴马一样都很‘美国’,”她说,“左翼人士喜欢说‘他一点都不美国’,但事实上他是的。如果你看看美国历史,就不会为特朗普那么受欢迎而奇怪了。”
她说,由于政治变得更加包容、种族多元化,而且女性拥有了更为公开的权力,人们感到“非常受威胁”。因此,卡玛拉·哈里斯成为首位当选副总统的黑人女性,这一胜利就更加令人激动了。“谈论她,谈论今天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不去想四年或八年后可能发生的事——她甚至可能成为总统,” 阿迪契说,“即使只是象征性的,因为领导的象征性质很重要。”
之所以有这次交谈,是因为阿迪契在庆祝百利女性小说奖25周年的“赢家中的赢家”奖项的公开投票中获胜。2007年,奖项由Orange公司赞助时,她凭借史诗战争小说《半轮黄日》击败了许多当代小说巨著拔得头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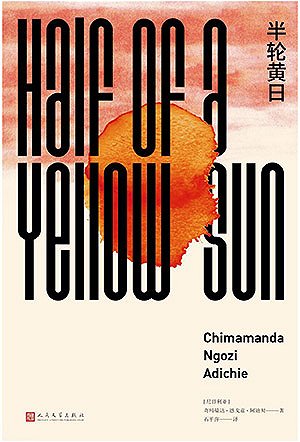
《半轮黄日》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石平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10
我们分别在伦敦和拉各斯,用Zoom视频通话,在2020年,这种谈话方式已经变得再熟悉不过了,因为网络连接不畅和孩子的影响,谈话一再被打断。今年对阿迪契来说尤其艰难,她失去了两个姑姑和她深爱的父亲,她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统计学教授——也是尼日利亚第一位统计学教授,今年6月意外死于肾衰竭并发症。疫情意味着她无法返回尼日利亚,而伊博人传统的葬礼也不得不推迟到10月份。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令人心碎的文章,题为《悲伤札记》,文中描述了父亲去世后,她与家人进行的一次“超现实”的视频电话交谈。“我们所有人都在哭泣、哭泣、哭泣,我们身处世界的不同地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敬爱的父亲,现在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今天她穿了一件亮紫色的T恤,上面用伊博语写着“我父亲的女儿”,这是她自己做的几件T恤之一。“我发现这真的很治愈。我设计的T恤数目多到荒唐。我穿上它们,心里就舒坦了。” 与她的短裤和上衣相当不协调的是,她的头发经过精心设计,那是为百利女性小说奖拍摄照片而做,这一组合拼合出了她“通过眼泪而假装”的强烈感受。一开始,她会冲动地想给父亲打电话,和他聊聊乔·拜登。在她获得新奖项之后,他往往是她第一个通知的人。但此时能给母亲打个电话已经使她欣慰,“让母亲看上去高兴些,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我也真的很开心了,”阿迪契眼含泪水说。
成立25年来,百利女性小说奖旨在“反映世界各地女性的声音”,其口号是“卓越、创意和平易近人”。阿迪契认为这个奖项帮助她找到了主流读者:她的第一部小说《紫木槿》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在暴君父亲和军事政变的双重打击下成长的故事,这部小说于2004年入围奖项,“使人们得知了我的存在。”三年后她凭借《半轮黄日》获奖时,这部小说并没有被视为“非洲小说”或者“女性所著”的小说,而仅仅是“小说”,她说,“我真的很感激。”

谭蒂·纽顿和切瓦特·艾乔福在《半轮黄日》(2013)中 图片来源:Monterey Media/Allstar
从那以后,她与希拉里·克林顿同台,与奥普拉·温弗瑞一起饮茶,她的书被学校定为主要阅读书目。在2012年的TED演讲《我们都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之后,她无意中发现自己成了现代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影响力青云直上,发言被印刷成册,分发给瑞典每一个16岁的孩子。很难想象还有哪位作家的歌词可以被碧昂斯的歌曲借用,被迪奥印在T恤上。如今,现年43岁的她被选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女性小说中的“最优秀者”。
她无法解释为什么《半轮黄日》经久不衰——这本小说出版13年后,读者们对它的喜爱超过了莱昂内尔·施赖弗的《凯文怎么了》、安德里亚·列维的《小岛》以及今年的获奖者麦吉·奥法雷尔的《哈姆内特》等畅销书。阿迪契自己也喜爱这部作品。“是它让我相信了一些神秘的东西,我注定要写这个故事,我祖父的灵魂希望我这样做。”
如果没有她的父亲,这本迄今为止阿迪契“最私人的”小说是不可能完成的。故事发生在1967-1970年的比亚法拉战争期间,她的祖父辈死于这次战争。《半轮黄日》来源于成长于战后的阿迪契从小所听到的故事,其中很多故事都是她父亲讲给她的。“他那时候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在使用现在时态后又纠正了自己,“我读了很多关于那个时期的书,但我得说,我从书中得到的是事实,但从人们告诉我的故事中我得到了真相。”书中发生的所有恐怖事件都是基于真事,包括她父亲的书在自家前院被焚毁。“对学者和知识分子说‘去你妈的’是一件非常卑琐、丑陋的事情,失去心爱之书这种事情我想象不出。”
阿迪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时才终于开始写作《半轮黄日》,以极度专注的笔调完成此书。她整天都在写作,只有偶尔跳绳时才会停下来;除了出门购买食材,她几乎寸步不离巴尔的摩的那间小公寓。有一天她冒险去了商店,惊恐地发现这座城市已经被入侵的知了所控制,而这件事已经上新闻好几天了。写到一半时,她“需要沿着祖父曾走过的路走下去”,于是她回到位于伊博兰那苏卡镇的父母家里写作,那是她长大的地方。自始至终她都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她意识到,对许多人来说,“这本书不仅是文学,也是历史。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历史尽职尽责的女儿的工作。”
阿迪契的传奇还包含了这么一段故事,她的偶像奇努阿·阿切贝在小说尚未出版之前就说她是“一位具有古代说书人天赋的新作家”。阿迪契的编辑通过电话把他的话念给她听。“老实说,我记得当时我想的是,就算这本书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他这句话)就够了。”
她的下一部小说《美国佬》于2013年出版,以温暖、诙谐而又愤怒的视角审视了在美国做黑人意味着什么——“我去了美国,我必须学习关于种族的东西。”小说以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为背景,营造了一种愉悦的氛围。最后,女主角伊菲麦露被欢迎新当选总统的“光芒四射、充满希望的人群”迷住了,“在那一刻,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美国更美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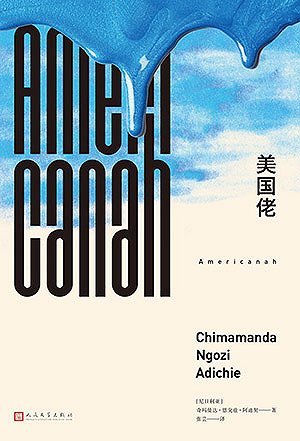
《美国佬》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张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1
尽管她对美国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在特朗普执政的过去四年中,她对美国的仰慕有所减弱,因为她“看着美国变得普通起来”,但阿迪契和伊菲麦露一样尊重美国的理念。“这几乎像是一种个人的损失。突然间,曾经我认为闪光的东西不再耀眼。突然之间,美国成了一个我们可以嘲笑和蔑视的地方。”
她希望拜登能引领公共文明的回归。“我真的很兴奋,全国的讨论听起来将不再像是孩子气的骂人。讨论的门槛降得如此之低,这是一种悲哀,”她说,“如果你是尼日利亚人,有些事情你就会很熟悉,你不会想到它们竟会在美国发生。特朗普向我展示了民主是多么脆弱,我们所认为的规范是多么脆弱。”
总体而言,她对美国怀抱希望吗?“我现在还不能回答。如果我今天回答这个问题,鉴于我有点兴奋,我就会对你撒谎。” 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乐观理由,是“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兴起。“至少美国左派现在愿意真正参与到种族议题中来,(示威者)促成了对话,促使一些有形的事物发生变化,促成行动。感觉像一个真实的、原始的运动。我感觉到,年轻的黑人同胞正把他们的痛苦宣泄出来。”
她谨慎地避免了她所认为的左派的“自以为是”。她说,她可以塑造出一个欣赏特朗普的角色:“作为一个小说家,这赋予我一种情感逻辑。”她已经借梅拉尼娅·特朗普“取乐”过了(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中),阿迪契为她感到“一种同情”,尽管她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太善良了”。

《亲爱的安吉维拉》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陶立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6
上次与阿迪契谈话还是在2018年《亲爱的安吉维拉》出版时,那时她发表了一份培养女权主义女儿的宣言,不久后她站在了她所称的“美国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的错误一端,因为她评论道:跨性别女性的经验不同于那些生来就是女性的女性。她不赞同“取消文化”(引号为她本人所加)。“有一种你不被允许学习和成长的感觉。宽恕也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太缺乏同情心了。我们美妙而复杂的人类自我有多少正在消失?”她问道,“我认为在美国,最糟糕的审查就是自我审查,而这正是美国向世界各地输出的东西。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这种叙事:你说错了话,就必须立即被钉在十字架上。”由JK·罗琳关于性和性别的文章引发的“全部噪音”她都很感兴趣,今年早些时候,在她看来“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重申一次,JK·罗琳是一个进步的女人,她明确地代表和相信多样性。” 她指责社交媒体造成了这种谴责,她认为,“(这)残酷并且悲哀。就思想而言,它原本就很无趣。正统观点是,你想着什么话就应该说出来,这太无聊了。一般来说,人类的情商足够高,当有些话来者不善时,人们是能够知道的。”
尽管成长于黑暗的政治环境中,但阿迪契关于童年的描写却闪耀着爱与欢笑;年少又聪明的她总是在智力和情感上得到支持。这使她无畏无惧。“因为我有家人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不能说出我的想法,即便我会因此而让别人不高兴。” 她的兄弟仍然会对她在尼日利亚引起的轰动抱以嘲笑,当人们想和阿迪契合影时,他们就会翻白眼。在美国的作家圈子里,她发现自己“几乎感到一种内疚”,她想知道,把作家视为不快乐童年的产物,这种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东西。“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多很多问题,没错,”她笑着说,“如果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无法想象事情会有多糟糕。”
但现在,她的世界已经改变了。“我父亲真是最可爱的人。” 她回忆起姐姐在一月份举办的乔迁派对。“每个人都对2020年满怀希望。我的父亲和姑姑都在。光想一想三个月之后她就会撒手人寰,5天后我父亲也离我而去,就觉得很怪异,”她说,“我真的感觉自己被重塑了。我被悲伤重塑。”尽管拉各斯已经很晚了,她还是要去给女儿读一个睡前故事,然后她要开始读很久没读过的《半轮黄日》:“我想回到过去,找到曾经的那个我。”
(翻译:马元西)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