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已有三代职场母亲。我的祖母在战争期间抚育着10个孩子,依靠为海员清洗衣物勉强维生。她在12岁时离开学校,从此成为了以祖父为生活中心的家庭主妇。到了1950年代,我的母亲在14岁时辍学回家,起初在三个孩子尚且年幼时做些兼职工作,随后在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做全职会计。我的姐姐是在1970年代离开家门的,她受训成为了一名教师,婚后同样育有三名子女。姐姐从校长职位退休后享有社会养老金,她和祖母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
然而,这三位女性无一例外都经营着“双重生活”,努力在带薪工作和家务、育儿之间寻得平衡。她们所从事的行业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女性聚集领域。诸如杂役或清洁之类的洗衣房工作,一直以来都由社会中最贫穷的女性来承担;像我母亲一样受过些许教育的女性,倾向于去工厂、商店或办公室工作;而掌握了更多任职资格证的女性则往往会从事照料相关的专门化工作,比如护工或教师等等。海伦·麦卡锡(Helen McCarthy)曾在她令人印象深刻且刻画入微的研究《双重生活》( Double Lives )中说,“这世上并没有典型人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部优秀的历史作品也展示出了人们的个人生活具有代表性的一面。
双重生活始于19世纪中叶,但在当下的现代社会最为有利。如今有四分之三的英国母亲同时在职场工作,这和维多利亚时代相比起来称得上是一个惊人的转变。一位母亲想要独立挣钱的渴望,也在更大程度上被认可合法。然而尽管文化已发生巨变,尽管职场母亲已进军各行各业,她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依然从事着不稳定的低薪工作,工作时间要求异常严苛,难以抽身照顾孩子。维多利亚时代的前辈们制作服装、粘贴火柴盒,今天在家工作的母亲们则是在制作婴儿连袜,或是为贺卡粘上水晶。

1935年英国默西赛德郡莫斯顿地区,费伦蒂公司(Ferranti)收音机零件组装车间 摄影:Daily Herald Archive/SSPL/Getty
直至20世纪,包括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和妇女机构在内的大部分英国公众开始提出,育婴假应是女性的基本休假权利。步入职场的女性往往感觉自己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二选一。“好”的母亲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工作,被抛弃的妻子、寡妇或是单亲母亲才能得到怜悯。而“坏”的母亲之所以工作,只是因为自己想要这么做。麦卡锡由此提出疑问,这些观念究竟得到了多大程度的转变?以往人们认为,养家糊口的男性应该赚取足够多的钱,让妻儿待在家里才算理想和称职,这样的想法现如今已不再是主流。但今天的雇主和政策制定者依然经常假设“工作者”应是男性,社会福利条款也总是过多地将母亲和孩子的需求合并到一起,认为妻子应全盘依赖于丈夫。家庭,依然被认为是以母亲为主的空间,而非父亲。
麦卡锡是经济和社会历史记录者,但她也希望能对与职场母亲相关的思考言论做一些“肌理分析”。从这一层面来说,她做得非常出色。她对流行小说、报章杂志十分熟悉,对内阁备忘录、议会、雇佣法或社会学报告同样驾轻就熟。她从不将手头文本资源视作真理圣经,而是通过早期社会调查灵巧刻画着穷人的生活图景,将其展现为“数据与情绪并驾,经验主义与情感主义齐驱的跨类别混合”,总是能将职场母亲的声音提升到官方或非官方犀利评价之上的位置。
穷困潦倒的女性绝不仅是单纯的受害者。虽然大部分职场母亲投身工作是为了经济所需,她们也同样可以享受职场。在家工作的母亲能为自己的手艺感到自豪,工业雇佣者则可饱尝同事之情、自由之味。一位在英格兰中部果酱厂工作的年轻母亲,因为坦承自己不愿“整天呆在家照顾小宝贝”而受到了女性巡视员的责备。事实上,她也为后面几十年的女性说出了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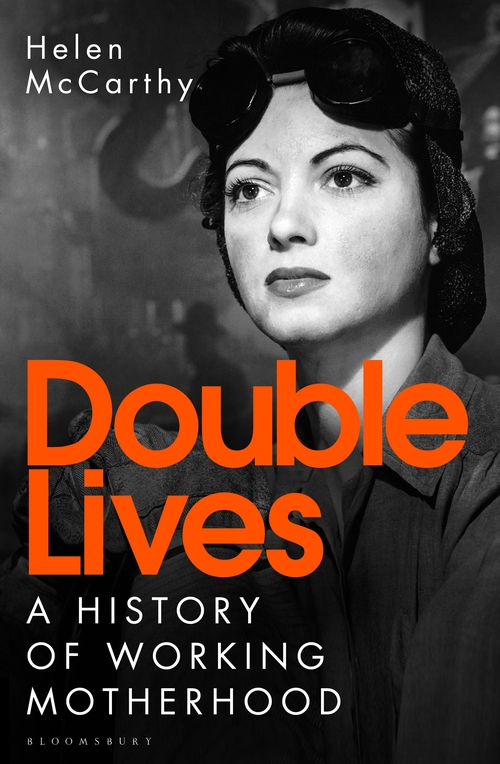
《双重生活》
20世纪早期曾有大批女性从事行政工作,但发展前景受到了婚姻的阻碍。战时管理机构召集起母亲们作为劳动后备军,倍加关注母亲们的需求,甚至为她们提供了工作间托儿所,但这也只存在于特殊时期。二战之后,得益于消费潮的到来,兼职工作规模也大幅度扩张,但雇主又凭着短期工的借口开出了不平等的薪酬。因为经常被视作婚姻和生育之间的权宜过渡期,或是身负大量家务工作的年长母亲,兼职工作者发现自己很难得到晋升机会、病假工资或是休假福利。情况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但长期来看,职场母亲的角色还是逐渐变得常见和可接受了。
麦卡锡的文字满是冷静的威力,但她并非中立。“循规蹈矩”的1950年代受到了特别指责。但在那十年里,包括我母亲在内的更多母亲,都在家庭之外的工作场合找到了满足感。双重生活者对于“母爱剥夺”理论充满怀疑,诸如约翰·鲍比(John Bowlby,英国发展学家,强调初生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在其人格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唐纳德·威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英国儿童心理学家,认为不间断的照料是早期成长中必须的)的理论,都常被用作打压职场母亲的棍棒。一部关于童年经历的历史显然会成就一本与众不同的好书,麦卡锡怀旧式的见证与分享也让这一问题更加开放。

自1945年起,政府就开始大量投资托儿所 摄影:Sam Frost/The Guardian
战后的数十年里,第二收入成为了一种骄傲和财富来源。人们更高的期待无可避免地与消费主义紧密连接起来,与为家庭或休闲娱乐的花费息息相关。如今双收入家庭同样继承了这一假设,即个人满足感和购买、拥有更多东西有着密切联系。自从可靠的避孕和堕胎手段出现之后,家庭规模大幅缩小。对于很多女性而言,这是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因为他们再也无需受困于无止尽的分娩。双重生活者很少谈及同龄人生育孩子的压力,也不怎么关注女性孕产迅速发展的商品化属性。
麦卡锡的最后一章以编年形式记录下了晚近的发展,包括雇佣法、薪酬斗争、反歧视政策等等。更多的职场女性在人生形色各异的道路上找到了自尊与经济独立,她们在公众场合更多地发声、被聆听。但她们的内心仍然充斥着罪恶感,经常精疲力竭。媒体对“自私的母亲”“工作过于卖力”和“想要一切”的女性、职场求胜心切的利己主义,往往过分夸大及扭曲,别说是女权主义了,这些做法根本就令人不悦。职业化的语境给女性带来了地位,但也导致男性市场化治理模式的再繁殖(剑桥历史学家麦卡锡在此主要指的是她的“直线经理”)。所谓的赋权所需的代价,是底层阶级的女性做着家务劳动,其中大部分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男性并没有做出那么大的转变,并不会投身家庭生活或抚育子女。在有些社会中,丈夫们依然更希望自己的妻子不要外出工作。
1945年之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都曾在不同时期投资发展妇产医院和托儿所教育。但在麦卡锡看来,虽然意识形态上有了变化,政府却仍然将女性利益和家庭利益视作同一种东西。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批判“家庭主妇”的角色被保留,也批判孩子们被珍视的如同财产。现在我们很少有人生活在传统家庭,但诸如“吃苦耐劳”之类的家庭修辞语依然时常被提及。作为保守派观察社会生活的基石,家庭依然被视作一种理想。而面对当前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过去的数次危机,女性,尤其是母亲,总是被要求在加倍努力工作的同时支撑起这种理想。
本文作者Alison Light是一位作家、评论家和独立学者。
(翻译:刘欣)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