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YouTube上的LifeHunter频道发布了一条视频,迅速火爆全网。视频中出镜的两人来到美食节上,乔装打扮成饭店老板,为蒙在鼓里的美食评论家装模作样地烹饪健康、有机的快餐,然而实际上盘子里的不过是麦当劳的垃圾食物。这些美食家津津有味地在镜头前将巨无霸大卸八块,大快朵颐的同时不忘描述口味怎样,肉质如何,津津有味,饕餮过后便是一番心满意足。这个视频本身并不是要控诉美食家都是骗子,而是告诉人们,他们并不高人一等。他们精致的味蕾和华丽的词藻在这时毫无用处,因为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洞悉他们不知道的内幕。
在这一点上,流行音乐和快餐有得一拼,二者都时髦流行,毫不比对方逊色。几乎每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曾从中得到享受,不管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负罪感。然而不管是快餐还是流行乐,往往都是文化和理性批评的对象,原因之一就在于,和粉丝相比,批评者一般都能够更好地阐释自己的感受。在音乐领域,这种高低文化之间的划分往往最为明显,也最有争议。
伪装一种音乐,比伪装食物要难得多。但人们看问题的观点才是最滑头的地方:如果说这个巨无霸被切得面目全非,但食客的心理预期更高的话,事情的结果会是如何?在新书《要听就听流行乐》( Switched On Pop ) 中 , 音乐学者、流行音乐播客主持人奈特·斯隆(Nate Sloan)和查理·哈丁(Charlie Harding)研究了二十一世纪的流行音乐,带着读者们一起灵魂拷问:今天的流行音乐到底为什么能响遍大街?其作用机制又有何重要性?
流行音乐何以流行,又为何重要,这个话题在最近几年愈发引人注目。2014年,《要听就听流行乐》以播客的形式进入大众的视角。最初的节目与另一个分析嘻哈歌曲的播客《剖析》(Dissect)合作,意在解构流行歌曲背后的技巧。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千禧一代——普遍认为,应该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流行文化:碧昂斯为什么被奉为天才,人们又为什么把酷娃恰莉称作后现代乐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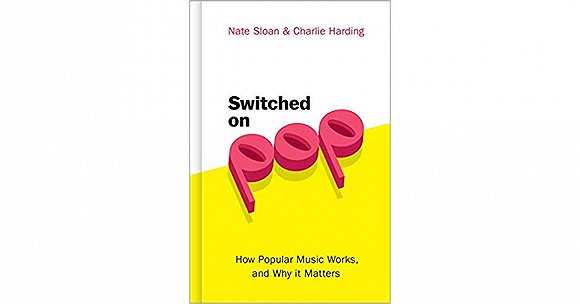
《要听就听流行乐》
奈特·斯隆/查理·哈丁 著
音乐世界的分裂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早在1941年,德国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就发表了关于流行音乐最权威的著作。他认为“严肃音乐”比流行音乐要来得优越,因为流行音乐是流水线和大众市场塑造下统一标准的产物,颇有些“音乐势利”的味道。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是“标准化”的——几乎所有流行音乐的内容、结构与旋律都趋于相同,流行音乐的创作有固定的规则,也有着明确的目标。这些特质就限制了流行歌曲,终究无法成就不朽。
在阿多诺发表作品的1941年,流行音乐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其内涵与形式还相对比较狭窄,与之相对的就是当时主流的古典音乐。到今天,流行音乐已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流派,囊括了不计其数的形式与文化,在全世界以铺天盖地之势力风靡起来,这时候,“标准化”已经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了。《要听就听流行乐》的两位作者还认为,流行音乐不管是在音乐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有其重大意义,即便放在阿多诺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亦然。
斯隆和哈丁将流行音乐的特质一一拆分,再分别列举歌曲作为例证。他们选取了过去二十年中的各类西方流行音乐,从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到DJ史奇雷克斯(DJ Skrillex),从流浪者组合(OutKast)到小甜甜布兰妮。两位作者认为,“想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表现21世纪流行乐的丰富与复杂是不可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确实为大众看待流行歌曲引入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斯隆和哈丁钟情于流行音乐爆红背后的社会语境,不亚于他们对纷繁艺术细节的热衷。书中有一章详述了音质对歌曲情绪和氛围的塑造作用,比如说歌手希雅(Sia)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和她故意凹出来的古怪英文口音就自成一派,在这十来年中引得越来越多人效仿。两位作者还把目光投向了美国饶舌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的《Swimming Pools》,分析了这种“陷阱说唱”(Trap,在美国南部俚语中指“毒贩的老巢”)中展露出的美国毒品文化。

饶舌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在歌曲中探讨美国毒品文化 图片来源:Santiago Bluguermann/Getty Images
一码归一码,《要听就听流行乐》的主旨并不是文化分析,而是音乐研究。在语言这个问题上,音乐学者常常卡在一个两难的境地:该用科学精准的术语,还是朦胧的隐喻呢?如果偏向前者,他们的作品在描述听歌情绪的时候可能会过分依赖笨拙甚至词不达意的修饰。但如果直接抛出隐喻的话,对读者的要求就高了,他们最好对各种专业术语、行话门儿清,而且这样一来,让音乐有得一说的情感体验很可能就从人们眼前溜走了。
要想让大众读者掌握音乐理论的概念,就不得不在阐述上费些功夫。不过这个苦差事也让两位作者有了更大的空间,在具体的音乐人和歌曲上舒展自己有启发性的见地。他们发明了“泰式催泪大法”(T Drop)这个词,用来形容泰勒·斯威夫特歌曲中名片式的“催泪旋律”(lachrymose descent)。从音乐性的层面上说,这个特征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她的作品总能成为口水歌,而从概念上讲,“泰式催泪大法”也为斯威夫特赢得了艺术上的美誉。
《要听就听流行乐》以播客的形式走进大众,为的也是让听者在相关音乐片段中,对斯隆和哈丁所说的音乐技巧得到一手体验。同理,当声音需要视觉呈现时,这本书插入了简明易懂的图例和趣味横生的歌星漫画。比如在讲解切分音的时候,读者就能看到拉马尔的脑袋在每一个小节上律动。这样的设计将细琐的理论灌注到具体可感的音乐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要听就听流行乐》插图
本书的语言和插图一样平易近人,如同老友之间的对话:比如贾斯汀·比伯在书中被唤作“B宝”。两位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流行音乐更加严肃,让古典音乐不那么令人生畏——罗西尼(古典作曲家)还会被阿芙佳朵(音译,一种包含咖啡和冰淇淋的甜点)呛到呢——同时,他们也展现了两种批评理论的不同风格,以及综合二者产生的振动效应。如果把古典音乐中的严肃性拿掉,它的魅力和影响可能也就消失殆尽了,Classic FM音乐广播电台的社交媒体推文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如果嬉皮笑脸地把十八世纪作曲家的东西插到新潮的流行乐评中,流行乐的个性韵味也一样会被打乱。
因此,《要听就听流行乐》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流行乐不能高冷,古典乐不能搞怪呢?另一方面,为什么流行音乐不能更加多元,没能容纳更多不同的范式呢?“如果说读者能察觉到,斯威夫特对‘泰式催泪大法’太过依赖的话,也许可以搬出法国作曲家若斯坎·德·普雷(Josquin des Prez)悠扬的音乐,两相比较。”斯隆和哈丁写道。这种交叉对比自然能带来不小的启发,但我们也该问一问自己,读者为什么非要扯上一位16世纪的经典音乐家,泰勒·斯威夫特本身不足以让人认真对待吗?
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中写道:“严肃音乐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每一细节的音乐感都来自于每一首乐曲的整体。”而流行音乐则反其道而行之,“每一细节都可以被替换,它的作用只像是一部机器的轮齿。”斯隆与哈丁在书中从未停止过对此的反驳,在这里,是时候祭出经典协奏曲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开头部分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钩子(hook,指一首歌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格兰德的《Break Free》原理亦然,这首歌中不仅有令人过耳不忘的旋律,更藏着不少“钩子”,传递着更为宏观的讯息。“‘自由自在(break free)’这个概念在这首歌中通过各式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Break Free》不仅是一个歌名,更是一种态度的终极任意门。”
美食评论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了麦当劳的垃圾食品,还觉得美味难挡,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咀嚼的是简单的料理,却下意识地认为这些都是高深复杂的手艺。在流行音乐的领域,情况可能恰恰相反。音乐总体上看是简单的、出于本能的哼唱,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但在这看似华而不实的表面之下,往往有大量复杂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来,《要听就听流行乐》通过分析,也许恰好证明了这些都是当代的“严肃音乐”。
(翻译:马昕)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