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乌尔曼的父亲耄耋之年时,开始将自己眼下的生活称作“终曲”。早晨醒来,躺在床上,伯格曼就开始细数自己的病痛——他允许自己每过10年就增加一种疾病,如果他的病症少于八种,就愿意起床,如果八种以上的病魔缠身,他宁愿卧床不起。然而这些小办法并不是绥靖主义,而更多是出于现实主义考虑,他老骥伏枥的决心几乎从未动摇。
乌尔曼的父亲就是伟大的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他倾注生命的最后几年留下的作品,是与女儿合力完成的。这本书捕捉到了生命临近终了之时,伯格曼对人生的感悟。在奥斯陆,乌尔曼强调了创作在伯格曼这一生中的中心地位。“在工作上,我们都清楚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们在创作——这点是好的。讨论起在这本书中我们要写些什么、以怎样的形式、如何叙述,这个过程妙趣横生。”他曾经开玩笑说,希望将这本书命名为“《埃尔多拉多山谷的性与死》(Laid & Slayed in Eldorado Valle)”,拍一部以之为名的电影是他未竟的愿望。
然而,最终英格玛没能实现这个小心愿。在他去世的12年后,乌尔曼的第六本作品《喧嚣》( Unquiet )面世了。这部作品结构松散,揉杂了回忆、虚构与冥想,但迸发着力量,讲述了伯格曼的生活,尤其是他对巴赫大提琴组曲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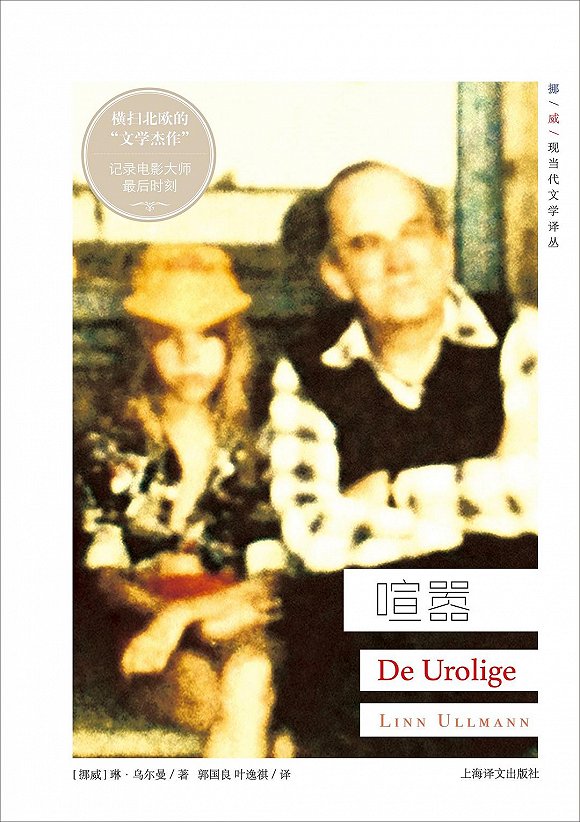
《喧嚣》
[挪] 琳·乌尔曼 著 郭国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
乌尔曼介绍说,“这本作品在另一本不曾被书写的书中涅槃。”随着这对父女满心欢喜地通信、打电话、多次相见,开始计划这本书的创作,伯格曼也一日一日变老了。正式落笔的时候,正值伯格曼去世前的那个春夏,这位老艺术家的身体状况急剧衰弱,随之而来的还有别的:“事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个月后,他的语言与以往不同了,我发现了他记忆的流失,他自己也能清楚意识到。仿佛他脑海中的所有窗户都敞开了,真实和梦幻四处飘忽,而父亲有时并不能辨别其中差异。”
这六卷两人对话的录音带在瑞典法鲁岛伯格曼的家中录制而成,这些录音是《喧嚣》这本书重要的线索,但多年来乌尔曼都不忍播放,她认为这声音是胎死腹中的作品“巨大惨败”的见证之一。“听这些录音带的时候,着实心痛如刀剜。所以我原本选择将它们束之高阁……我本该早些开始的,我本该趁着我们还能面对面坐下的时候提出不一样的问题,我本该用质量好一点的录音机来录制,因为这些录音带的背景音实在嘈杂不堪。我不该这么高嗓门儿说话。”最终她的丈夫,作家尼尔斯·弗雷德里克·达尔说服了乌尔曼从阁楼上翻出录音带:“既然你都开始提笔了,就不想听听这本书吗?”乌尔曼继续说:“于是我听了下去,将语音通过笔头记录下来,又将瑞典语翻译成挪威语,真是令人愉悦。”

琳·乌尔曼。图片来源:Kristin Svanæs-Soo/Kristin Svanæs-Soot
当然,这些最初的感受都是死亡难免引起的本能反应,是遗憾的体现——我们总认为,自己如果当时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今天的丧亲之痛就会有所减轻,或是能保留所爱之人生命中更多更切实的片段。在乌尔曼身上,这种感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是原始本能。
琳·乌尔曼出生于1966年,正好是伯格曼的经典名作《假面》上映的那一年。她的母亲挪威演员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n)也出演了这部电影,饰演舞台剧女演员伊丽莎白,因为在一次演出中忘了台词而在之后的数月中拒绝说话,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由护士阿尔玛(毕比·安德森饰)照顾。英格玛·伯格曼当时还在肺炎的恢复期中,仍然亲自编写剧本。脑中清晰浮动着两个女人的深夜,才思泉涌,速度飞快。这部电影的拍摄地是法鲁岛,随后他不仅在这里安下了家,更打造了自己的王国,不停地盖起新房,包括一家电影院和写作小屋。
这部电影为伯格曼和乌尔曼的合作拉开了帷幕,两人共同拍摄了10部电影,并开始了恋爱关系。此时的伯格曼47岁,结过四次婚,是8个孩子的父亲。丽芙比他年轻20岁,而且也是已婚状态。事实上,琳出生的时候,她的精神病医生丈夫就在身边。伯格曼与缪斯女神乌尔曼离开后,再次结婚了。他的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琳·乌尔曼在哈默斯度过了那个夏天。往后的日子里,她都与母亲为伴,居住在奥斯陆和美国。当母亲外出工作的时候,外祖母和来来去去的保姆们负责帮忙照看她。“我是伯格曼的女儿,也是乌尔曼的孩子,”她在《喧嚣》中写道,“但不是‘他们的’孩子,‘我们仨’是不曾有过的。当我翻看桌上的照片时,从未找到一张三人的合照——她,他和我。我们是无法组合的星群。”

伯格曼电影《假面》中的丽芙·乌尔曼。图片来源:Allstar/United Artists
这本书最后以何种面目呈现,慢慢地水落石出。第一人称叙事与小说化的用语交织,“那个女孩”、“父亲”和“母亲”这样的称谓穿插其中。有时候当我提到书中的一个“你”的时候,乌尔曼会善意提醒,这指的是“女孩”。即便是这种虚构写作式的叙事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乌尔曼否认她与父母是《喧嚣》的基石。“这些文字中间的微妙令我着迷。”她还表示雷切尔·卡斯克、黛博拉·利维、约翰·伯格、埃德维奇·丹蒂卡和艾米莉·狄金森都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舞蹈家皮娜·鲍什、默斯·康宁汉和作曲家约翰·凯奇也在她身上留下了不浅的烙印。
如果说伯格曼是贯穿全书的核心骨架,那么今年81岁的丽芙·乌尔曼则以血肉填满了这本书。伯格曼在哈默斯孤独内省,丽芙·乌尔曼则在奥斯陆、洛杉矶和纽约间穿梭,常有女儿相伴,后者在曼哈顿的酒店走廊里被舞蹈皇后玛格特·芳登拨乱了头发,收到过她妈妈的俄罗斯追求者的一罐鱼子酱。两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也反映了他们各自在文化中占据的一隅:“一个是传统的男艺术家,另一个是女演员;一个是凝视者,另一个是享受目光的人。”
乌尔曼记得自己小时候对母亲近乎绝望的爱,要是妈妈迟到几分钟,她就会痛苦不安。“我疯狂地爱着母亲,不仅因为她无与伦比的美——我用文字描述过这种美,生动、强壮、狂热,令人动容、让人渴望。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面对这种美只感到被击中的晕眩,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即便是长大成人,也无以言表,它令我绝望、油生向往,我意识到,如果这个人消失了,我也会死的。没有她我活不下去。”

1971年的琳与丽芙·乌尔曼。图片来源:Classic Picture Library/Alamy
我提到,拥有一个经常离开的母亲,一定很难熬吧。乌尔曼很快指出,丽芙·乌尔曼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职业女性,而且是未婚妈妈,永远活在公众的目光下。乌尔曼讨厌狗仔队照片中自己的样子,比如说当她独自乘机去见母亲的时候,总得在脖子上挂一个塑料文件夹:“我不想做个孩子。我不知道如何做孩子,对自己的儿童身份,我甚至感到一丝羞愧。”我问她,母亲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她什么都知道,”琳做了个怪脸回答说,“她是个艺术家啊。”
在《喧嚣》的结尾,这个16岁的女孩独自前往巴黎。她在那座城市的冒险,拼成了小说三部曲的第二部分。“女孩的模样定格在那里,”她解释说,“不再往前,也没继续拘泥于母女的故事。当你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老了,成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了。而我现在更老(54岁)。因此,我将从这种年龄的视角继续写。”
《喧嚣》首次在挪威出版时,一位记者提问,能不能抽出“五分钟”来讲讲小说中的虚构与现实。她笑了——五分钟不可能客观地分析二者。事实上,这项工程可能要花上一辈子。
(翻译:马昕)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