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琼·狄迪恩,1960年代的新新闻主义记者们是一群热爱自吹自擂的人,他们决心在所报道的故事中大做文章。诺曼·梅勒大吵大闹;亨特·S. 汤普森大发雷霆;汤姆·沃尔夫不那么大男子主义,但他总是洋洋自得;杜鲁门·卡波特则低声煽动。当狄迪恩称写作为“一种咄咄逼人、甚至是敌对的行为”或“暗中欺负人的策略”时,她可能是在对这种傲慢的兄弟会下定义。
从最新出版的《让我告诉你我的意思》( Let Me Tell You What I Mean )文集中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狄迪恩自己的策略更加隐蔽,甚至可能是一种被动的攻击。在一篇颂扬嬉皮时代地下刊物的文章中,她宣称了新程序下的意识形态:为了防范受人尊敬的大报及其“虚构的‘客观性’”,记者需要冒着“用‘我’作为主语”的风险。然而,对狄迪恩来说,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一开始拒绝使用第一人称,因为这是属于她的男性同事的自大特权。
作为一名小说家,狄迪恩说,她通常要先开始寻找一个她可以承担的叙述者身份。只有这样,她才能讲述一个故事。在她的新闻报道中,她更喜欢在外围徘徊。她不去采访南希·里根,保持着恭敬的距离,电视新闻组则走进去拍特写。在一篇关于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的文章中,她回忆起早期在《Vogue》时,她的低级工作就是“观察女人被拍”,不过在一次采访中,星光熠熠的模特抢走了狄迪恩的裙子,她只好蜷缩在雨衣中。这种既想观察又想保持疏离的欲望,让她对朋友托尼·理查森产生了警惕,因为他暂时没有剧本或电影可导演,便会抓住一种“戏剧性的可能性”,诱使来吃晚餐的客人大吵大闹,狄迪恩只好逃之夭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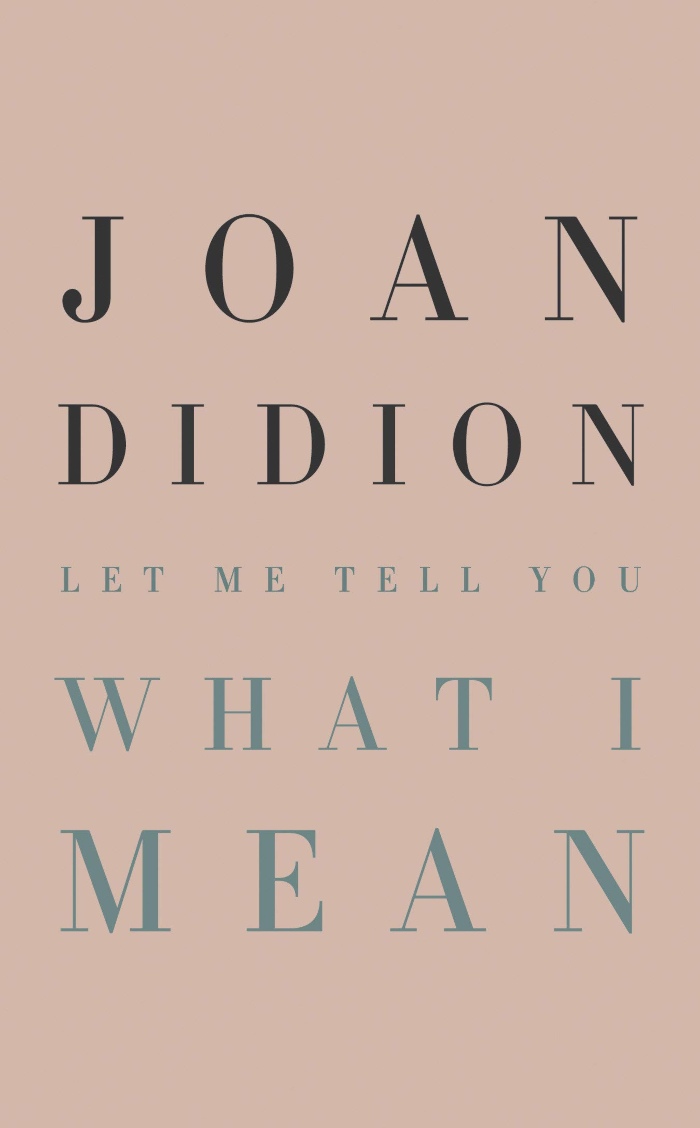
《让我告诉你我的意思》
这样的自我抹杀让狄迪恩为她称之为“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刷出来的致命羞辱”做好了准备,这句话也恰好捕捉了她写作时的紧张焦虑。文集里有两篇文章是自我羞辱的练习:在一篇文章中,她在大学申请被拒绝16年后继续反思。另一篇文章中,她将一篇被25家不同出版社拒绝的短篇小说的拒绝通知进行了选编。“我们不太会选择这样一篇小说,”《好管家》杂志回复说,“这完全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其他文章中,狄迪恩感叹身体上的无能和精神上的绝望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她患上了副伤寒,不得不在哥伦比亚的酒店房间里度过一星期——“那不是个适合发烧的地方”,特别是当酒店的发电机发生故障时。
思考着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照片中的虐待画面,狄迪恩猜测着羞辱的仪式,这不仅仅是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刷出来。她说,令梅普尔索普兴奋的是“无力感的高扬和死亡的诱惑”。难道类似的精神,能使狄迪恩从《奇想之年》中记录的骇人听闻的失去中幸存下来吗?她认为,梅普尔索普将秩序强加于混沌,将对称强加于淫秽。狄迪恩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她脆弱、退缩的人格是一种秘密武器,与诺曼·梅勒和其他人的狂妄一样英勇。
因为她对自己的弱点了如指掌,因此她对虚伪的眼光是致命的。在参观报业巨头赫斯特建造的加州城堡圣西米恩时,她发现了剥落的雕像和虫蛀的木制品,让她相信“无限的乐趣都在此时此地”;在1968年拉斯维加斯的一次军人聚会上,她任由老兵吹嘘他们在朝鲜的豪情壮举,却无意中听到他们承认,他们的儿子们目前在越南正面临危急情况,这并不是一次光荣的冒险;在向海明威的“浪漫个人主义”致敬之后,她对“他的个人大男子主义主张所带来的耻辱”私下吐露了一丝遗憾,并对他的继承人的唯利是图感到痛心,他们将家族的名字视为“英雄的品牌”,并通过授权生产一系列以野生动物园为主题的家居用品来变现。
这些文章越是细微,就越显得与众不同:它们是如此灵巧和神秘,往往——正如狄迪恩出色地分析海明威的风格时所说的那样——是 “刻意省略和隐瞒信息的张力”的结果。在她最早期为《Vogue》杂志撰写广告文案时,她以整齐但起伏的从句和组织“39个字母的简单句子”为乐。在她关于梅普尔索普的文章中,她以惊人的随意性宣布了这种极简主义的信条。她宣称,艺术家是“无中生有的人”。诚然,作家就像巫师,他们用文字来施展魔力。但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辛苦的,值得骄傲的结果是有所成就,是手艺的产物。狄迪恩笔下的一个句子,无论是坚持39个字母,还是用多个从句阐述可能性,都是神奇思维的奇迹。
(翻译:李思璟)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