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世纪初,正值图拉真统治鼎盛时期,此时古罗马帝国版图横亘亚非欧,统治时间比任何前现代国家都长。帝国将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收入囊中,南达撒哈拉沙漠,北至不列颠北部。到了格雷戈里大帝(c540-604)的时代,罗马巨人已然四分五裂,君士坦丁堡成为最后的堡垒,控制着一些分散的领土。随着罗马秩序的崩溃,西欧分裂成兵荒马乱的几个日耳曼王国,而南部的伊斯兰大军正过关斩将,蚕食着帝国所剩的疆土。公元一世纪栖居着100万人口的古罗马帝国,此时只剩下2万臣民。
正如凯尔·哈珀(Kyle Harper)在书中所写,罗马的陷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倒退”。1984年,一位德国古典主义学者枚举了200多种压垮帝国的解释。军事扩张让国家不堪重负、对奴隶劳动力的过分依赖、挥霍的财政支出、为了讨好部分公民而实施的“面包和马戏”绥靖手段和愚民政策,以及因此产生的苛捐杂税,甚至基督教的兴起也是导致罗马衰退的共犯。毫无疑问,罗马不是一天倒下的。以上的因素推动着罗马一步步走向漫长的下坡路。这些说法的共同点在于,人为因素站在舞台的中心,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决策权也许根本不在人类手中。哈珀的观点一鸣惊人:气候变化和恶化的大流行病使罗马经营了好几个世纪的全球网络最终崩溃。
罗马帝国崩溃的余波还震碎了一个经典的世界观。斯多葛主义原本在罗马贵族和行政官员中广受推崇,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都为之背书。斯多葛主义认为,人的理性在“依照不变的自然而生活”中实现。在这种观点下,世界上不会产生新的恶,比如说没有新的疾病,因为它会打得理性人类一个措手不及。在这种世界观里,通过人与宇宙和谐融合,便能成就一种圆满道德的生活。
然而一连串流行病的爆发挑战着这一经典观念。“安东尼瘟疫”始于公元165年,在公元180年达到顶峰。当时的罗马史家卡西乌斯·狄奥记载,疫情最严重时,罗马一天就有2000人因病去世,整个帝国的死亡人数达到百万。根据哈珀的估算,这场大流行病可能夺走了约700万人的生命。奥勒留百思不得其解,这场灾难狞笑着推翻了他理性宇宙的信念,于是这位皇帝在从斯多葛学派中抽身,写下了《沉思录》,将每一天当作生命最后一天来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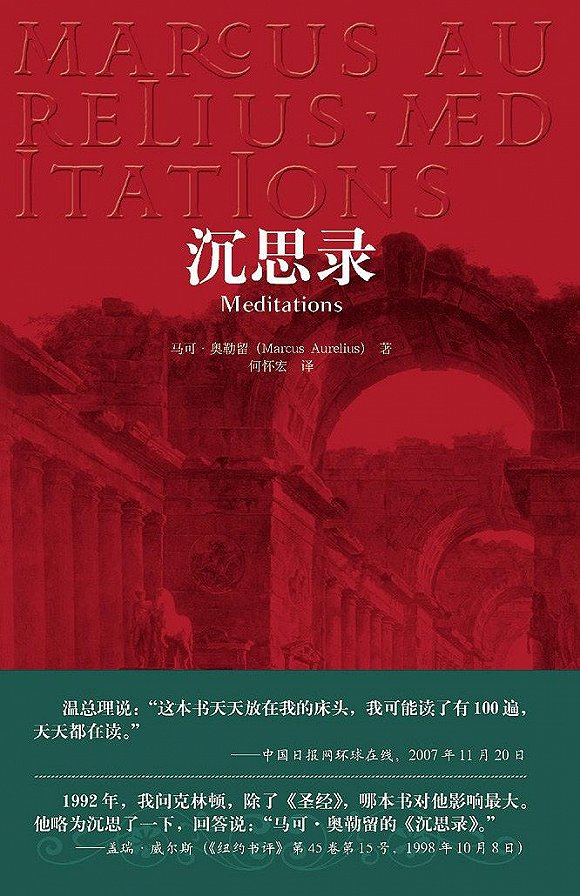
《沉思录》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著何怀宏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2
三世纪中叶,至今病原仍然不明的塞浦路斯瘟疫又一次撼动了罗马帝国的根基。到了格雷戈里的年代(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推测为腺鼠疫,和中世纪的黑死病相似)爆发,许多人已经开始认为,世界本质上就是混乱且与人类对立的。结果是阿波罗神受到狂热崇拜,基督教也迅速起飞。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瘟疫,基督教有可能就不会被这个破败的帝国采纳为国教。
正如哈珀所言,伴随着罗马的沦陷,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古罗马时期,地球的生态并没有比今天稳定多少,而罗马人自己更是环境的改造者。
罗马文明似乎骨子里就有景观改造的潜力。农业的发展带着人类文明开疆拓土,来到了更加适宜蚊子生活的环境。砍伐森林导致积水增多,原本的树林成为洼地,更是开辟了蚊虫的乐园……凡此种种,无不看出古罗马人就是环境工程的领头羊。
然而在古罗马,人为因素还不足以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永远是一个外在元素,是打破一切游戏规则的超级王牌。气候的改变通过外力重塑了人类社会的人口组成,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社会和国家等更加复杂的组织之所以能出现,也是托它的福。”地球公转路径、黄赤交角以及自转的微小变化恒久改变了这颗行星的气候。更新世时期,地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直到大约1.2万年前进入全新世,地球逐渐回暖,才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和管理制度。即使在那时,太阳运动也在与地球内在的气候的相互作用,扰乱着人类的生活模式。比如说,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晚古典小冰河时代,瘟疫肆虐长达150年,季节周期紊乱,农作物歉收。然而从总体上看,罗马人是幸运的。在帝国的鼎盛时期,气候相对稳定。
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的能动性在这个处处互联的帝国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催化了罗马的衰退。罗马贸易网络长,来往密切,粮仓里啮齿动物茁壮成长,感染也顺着这些轨道进入罗马。此时人口空前密集,大部分居民都挤在城市中。肺结核、麻风病和大量热症在地方上时有发生。罗马帝国疆土广阔,她脆弱的子民也更容易受到十万八千里外的疾病感染。罗马瘟疫是全球化最早期试验的一个副产品,罗马帝国巅峰时期,大流行病的潜在因子不可避免地篆刻在了其社会结构中。
罗马遭到了自然的痛击,最终让她倒下的并不是自然资源的匮乏。残酷的强权统治、技术创新与高超的政治斡旋多管齐下,罗马帝国成了十八世纪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一个例外——人口过剩,食物短缺并没有让帝国崩塌。“(然而)城市聚居地的密集人口、长年累月的景观改造、帝国内外的交通联系网络,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微生物友好的环境。”罗马文明的伟大成就中就隐藏着令她崩溃的因子,帝国的远距离统治、互联共通导致她在疾病面前脆弱不堪。近乎宇宙秩序运行的社会给了瘟疫可乘之机,最终全盘倾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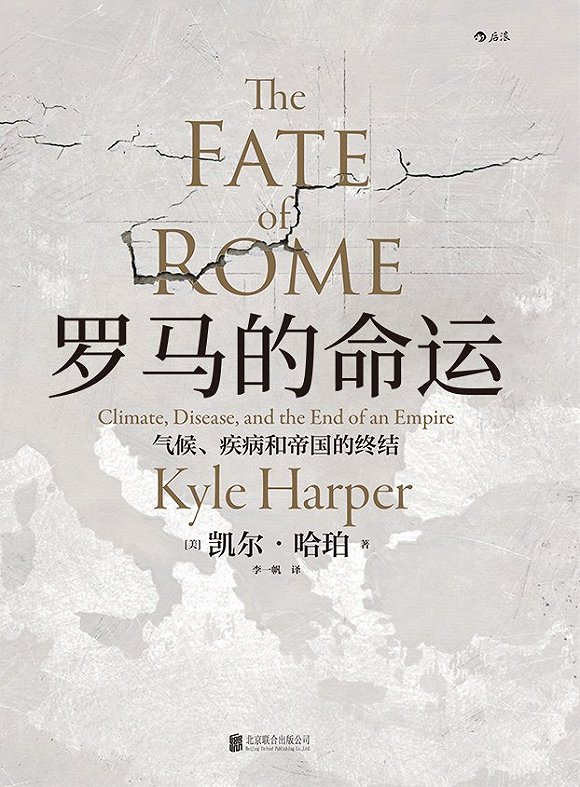
《罗马的命运》
凯尔·哈珀 著 李一帆 译
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6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副院长凯尔·哈珀的《罗马的命运》放到今天正当时——读者们可以在前所未有的失衡生活中调整自己。这本书在2017年出版,当时其价值还没有因为疾病因素而加成。随着新冠疫情持续发酵,这位《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继承者从另一个侧面解读了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令人大开眼界,心生敬意。
哈珀理论的一个关键是,即便你穷尽了智慧,也无法避免罗马文明的崩溃。当罗马人平地起高楼时,他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正创造一种让疾病以空前速度传播的环境,他们也并不了解正在悄然发生的气候变化,二者结合会带来怎样的毁灭性结局,更是无从知晓。到了格雷戈里大帝统治时期,罗马人并不因末世论而恐惧,也没有世界末日的宗教束缚,这不足为奇。
新冠疫情爆发的今天与当年的罗马人生活的世界已经相去甚远,人类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已经相当充分,更别说主要的气候变化趋势都是人为因素在推波助澜。病毒学是一门现代科学,疫苗是现实的解决方案。可以想象,新冠病毒可能已经不如早期病毒那样致命,甚至有可能像2003年的非典病毒一样,消失遁形。不过这些猜想仍然缺乏科学的支撑,基于此投机的推测制定政策无疑是鲁莽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新冠病毒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用不同的数据模型预测其传播轨迹和致命程度,会生成不同的结果。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知识的稳定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但是科学探究始终不能排除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人类福祉受到严重威胁时,会引发思想严重地震,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能比自己想象中更接近罗马人。
不可否认,古今之间存在种种相似之处:新冠疫情也出现在全球化高峰时期,而且全球供应链紧绷,人们在疫情面前几乎没有抗震能力;另外,新冠病毒也是大规模环境改造背景下出现的。马尔萨斯人口动态的一个不详转折点是,人类向居住条件较差的地区迅速扩张,比如说曾经由采集狩猎者聚居的亚马逊地区。当这些地区转身开发农业,当地的生态受到严重干扰,野生环境迅速消失,动物传播的疾病也因此更容易转移到人类身上。人口增长给这一感染链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哈珀在书中表示,“人口数量的增长……为地球上各种微生物的共生者重写了游戏规则。”大规模空中旅行加速了野生动物市场和工业农场的疾病传播。和古罗马如出一辙,新冠疫情前的全球秩序,也孕育着大流行病的胚胎。
病毒对人的主流信仰系统也会产生影响,在这一点上,今天和古罗马有着相似之处。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的混合双打震碎了当时统治者的世界观,今天的病毒也动摇了我们的现代性理念,即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塑自然世界。所谓不管人类野心再大,都无法逾越自然的约束,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异端邪说。在很多人看来,似乎除了人类的思想和感受外,一切都是虚无。但病毒却不符合人类发展的目的,是对这种偏执的现代信仰沉重一击。正如哈珀所言:
可以预料,随着流行病的蔓延,人们的世界观也将发生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因其发生剧烈变化,思想也不会一成不变。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太多现实主义的思考。大流行病打破了人类前进的既定叙事,揭示且推动了更深层的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仇外心理肆意发散。连过去标榜着自由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的部落主义和激进的意识形态都蓬勃发展;阴谋论比比皆是,假新闻和江湖疗法随处可见。政治冲突和文化战争如火如荼,而不论人类信仰如何更迭,这种病毒依然按部就班地传播,警示着世人,疾病不会遵守物质世界的规矩。

6月7日,千万人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参与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游行。图片来源:Michael Nigro/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由于封锁成本不均,政府的失效和混乱的管理,社会内部的分歧加剧,最初齐心协力对抗疫情的团结已经破裂。原本人们对社会隔离政策的支持正在磨损,更糟糕的情况是,这种秩序如今已经崩溃。令人发指的种族主义造就惨剧,一名手无寸铁的非裔美国人被警察在光天化日下杀害,引发全球抗议。但病毒并不关心受害者是种族平等倡导者还是信奉白人至上,不管你是投机的抢劫犯抑或只是跑去切尔滕纳姆看赛马。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是否更容易遭到杀害也没有任何意义。对病毒而言,社会各阶层都可以是受害者,所有的群众集会都会成为超级传播场合。
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敲响警钟。1918年9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正酣,流感流行似乎正在退场,费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以支持战争,二十万人走上宽街,为游行队伍加油打气,其中不乏流感的感染者。10月3日,市政当局宣布封城。10月5日,死亡人数约2600。一周后,统计数字超过4500。短短六个月,该市有两万人死于流感。在过去的几周中,美国和其他国家至少进行过数十次甚至数百次这样的群众聚会。虽然有的人保持了一定的社交距离,新冠病毒与流感也有所不同,但即便如此,风险也是不容小觑的。
大流行病的传播没有预定的轨迹,但由于今天我们已经有雄厚的医疗资源,不会重蹈古罗马前辈的覆辙。然而,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人类知识已经指数增加,但我们真的比巅峰时期的罗马人更理智吗?亦或许我们是不是比他们更容易陷入集体混乱的状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答案可能会逐渐清晰。
本文作者John Gray是《新政治家》首席书评人。
(翻译:马昕)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