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只猫是一种什么体验?哲学家约翰·格雷半辈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当他还是英国南希尔兹的一个孩子时,就已在家中养猫。如今他与妻子、日本古董商Mieko住在巴斯。他们养过四只猫:“两只缅甸猫姐妹,索菲和莎拉,以及两只伯曼猫兄弟,杰米和朱利安。”它们中最后在世的一只——朱利安于今年初去世,它活到了23岁。格雷目前没有猫。他绝不是一个多情的作家,但他的新书《猫的哲学:猫与生命的意义》(
Feline Philosophy: Cat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暂译)却是为了纪念他与猫的共同的智慧而写的。
这些年来,其他哲学家也被猫所吸引。薛定谔有盒子里的猫理论。蒙田曾发出著名的提问:“当我和我的猫一起玩耍时,我怎么知道它没有在和我一起玩耍?”格雷说,理性主义者笛卡尔曾经“把一只猫扔出窗外,以证明人类以外的动物缺乏意识;他总结说,它的恐怖尖叫是机械反应”。
这本书成书的推动力之一是与一位哲学家的对话。这位哲学家向格雷保证,他“已经教会他的猫只吃素食”。(格雷只提出了一个问题:“猫有没有出过门?”答案是肯定的。)当格雷告诉另一位哲学家,他正在写我们可以从猫身上学到的东西时,那个人回答:“但是,猫没有历史。”格雷问道:“这一定是个不利条件吗?”
格雷写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如何看待“就算狮子能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们”的说法。动物园管理员约翰·阿斯皮纳尔回答说:“是他花的时间还不够长。”我问格雷,如果猫能说话,你认为我们能理解吗?
约翰·格雷的猫朱利安于今年初去世 图片来源:John Gray
他说:“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实验。当然,这不是科学的探究。但是,如果你与猫非常亲密地生活了很长时间(这需要花上很长时间,因为它们建立信任的速度很慢,与你真正交流的速度也很慢),那么你或许能够想像它们有着怎样的哲学。”
格雷认为,我们主要是出于焦虑而追求哲学,我们是在一个混乱而令人恐惧的世界中寻求某种宁静,向自己讲述或许能够提供平静幻想的故事。他指出,猫不会意识到这种需求,因为只要不感受到饥饿或威胁,它们自然就会恢复到平衡的状态。如果猫要给建议,那只是为了娱乐它们自己。
格雷的读者会将这本书认作《稻草狗》的后记或结尾。这本2002年的畅销书优雅地解构了西方哲学史,以及其虚无的信念——“人类在其他物种之‘上’,并且不受自然的限制。”那本书特别将矛头指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信念:人类带来自由民主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稳步向前的。这本书问世时,布什总统正在伊拉克寻求“政权更迭”。这本书特别令人不安。此后的二十年间,它的论点几乎像是预言——理性思想的发展可能无法在基础的种族直觉、环境破坏或人类的愚蠢面前为我们提供任何持久的保护。
格雷从不认为他的书是本绝望的手册。他的主题是谦卑,他针对的,是自认为自己不止是“对庞大且不断变化的问题的不确定的零星答案”的任何意识形态。这本关于猫的书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写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在读书的时候总是拿着一支笔,你一定会频繁地勾划、做感叹号标记,并像猫一样发出享受的声音。格雷冷静地写道,“意识被高估了;理性主义的缺陷是,人们相信人可以通过应用理论来生存;人类会很快失去人性,但猫永远是猫。”他总结出了10个猫咪给焦虑、不快乐、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关于“如何不笨拙地生活”的提示。这些提示包括但不限于:绝不跟人类说理,不要给自己的苦难寻找意义,为了享受睡觉的快乐而睡觉……
有人批评认为,《稻草狗》推翻太多,建树太少。格雷是否将这半认真的十个点(“就像猫的那种半认真”)视作针对《稻草狗》的批评的回应?
格雷热情而友好地说,“是的。”他的声音仍然带有英国东北部口音的曲折感(英国电视剧《当船进来时》的主题曲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他说,“许多人不喜欢《稻草狗》。人们批评我一棒子打死了所有哲学。一些并非哲学家的人给了我很好的反响。例如,这些年来,有三位战地记者说,适应他们所目睹的创伤是他们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而我的书以某种方式帮助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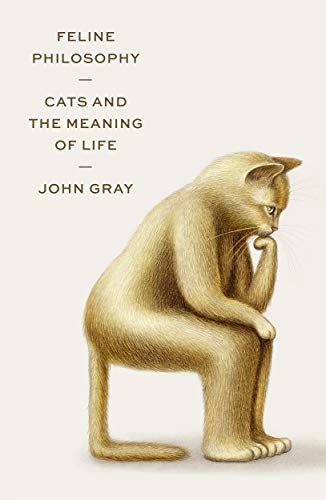
《猫的哲学》
或许,这本书帮助了他们,是因为它消除了使可怕、悲惨的事情变得有意义的压力?
我们原本计划是在巴斯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并坐在室外进行访谈,72岁的格雷不喜欢室内。但天气预报表明,那样的话我们会被大雨淋成落汤鸡,所以我们像猫一样退到室内,并选用了Zoom。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格雷的书是帮助人们应对大流行导致的奇异疏离的完美读物。他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
他说:“我试着重现我对我的猫,朱利安的回忆——不要活在想象中的未来中,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将如何发展。在大多数地方,当然还有我们这里,政治都是一团糟。但是我认为,‘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应对方式’这件事反映出一些深刻的东西:即使是最发达的知识体系也总是会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当多米尼克·卡明斯(现任英国首相首席特别顾问)开始宣传“超级预测”的力量时,政府却似乎无法预测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此时的格雷一定会警惕起来。(超级预测指的是某些特定的人进行的预测,这些人的预测被证明比一般大众和部分专家的预测更准确。这些“超级预测者”往往采用现代分析和统计学方法来进行预测。)
“是的,他们确实如此。我认为‘超级预测’仅在特定领域中是可能的。几乎没有人预测到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真正的重大事件甚至都没有被认为处于合理可能性的范畴之内。我记得,在2000年代初,我曾问过许多经济学家和大佬,是否可能发生全球银行业危机,这个想法被普遍否定了。只有一个人说过:‘我不这么认为,但这说不准。’”
约翰·格雷说,2号高速铁路(HS2)始终是一个错误。现在,“很多人再也不会出门上班了,”它错上加错。图片来源:Maureen McLean/REX/Shutterstock
如果我们在想象未来时感到无望,那么我们是不是完全可以重塑这突然变得异常的当下,并让当下重回正轨?“这一切确实发生了,但我认为,这部分基于许多人仍然认为还存在‘正常状态’的假设。我认为这完全没有道理。这6个月中发生的某些变化可能会持续存在6年或60年。这其中的部分改变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可能是良性的,比如英国,因为英国仍然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对巴西或印度的边缘人群来说,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格雷拿英国的2号高速铁路举例。“由于成本和环境上的问题,2号高速铁路始终是一个错误。但是现在它显得更荒诞了,因为很多人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出门上班了。政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实践中,个人比政府更容易适应激烈变化的环境。”他把话题引回我们的主题,说道,猫不会深深地迷恋某些故事。“当然,你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智力,但我认为它们只是不感兴趣的可能性也很大。”
由于缺乏对执着于特定故事的兴趣,这些年来,格雷在政治上走入了特殊的境地。他在英国泰恩赛德一栋坚固的旧劳动救济所建筑中长大。他的父亲在码头上当木匠,母亲则待在家里。格雷在1960年代目睹了其社区被破坏——维多利亚时代的街道被推倒,居民搬进了由后来因相关事务入狱的工党领导人T·丹·史密斯主张建造的简单粗暴的“乌托邦式”计划住房中,这使格雷对所有兜售进步思想的宏伟项目产生了持久的不信任。
从那时起,他就形成了一种信念,“政治是对永久性的和反复发生的人类邪恶行为的一系列临时、部分的补救措施。”他最有智慧的两位朋友分别是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和小说家JG·巴拉德。前者全家从苏联逃离到了英国,后者则在日本监狱里度过了童年。他们都促使格雷相信,任何自认为垄断了智慧的政治运动,都有古拉格或集中营的成分在其中。(作为其最有名的讽刺行径,格雷曾模仿乔纳森·斯威夫特,写了一篇“温和的建议”,呼吁西方民主国家为保护人权应紧急重新引入酷刑;随后不久,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发生。)
格雷的投票策略一贯灵活,在任何时刻,他都会投给两派政治势力中不那么邪恶的一方。他说:“如果当时可以的话,我一定会在1945年支持艾德礼政府。”但到1970年代,他认为战后的工党政策已经变得愚蠢和腐败。他站在了与大多数学院相对立的立场上,支持撒切尔作为英国政治历史上的必要修正。“但是,到了1989年,它又完全变了味。我从1987年左右就改变了立场。”他曾一度支持新工党,但后来,出于相同的原因,他又摈弃了该党的主张。
他说,在上次大选中,他把票投给了保守党。这是因为,他认为英国应当完成脱欧。现在,他嘲笑“民主人士”的妄想虚伪——他们希望进行第二次全民公决,“但人们已经进行了一次白纸黑字的投票!”在他看来,这种事情永远都无法圆满地结束,欧盟本身及其宏伟的计划和项目也是如此。

抗议者呼吁对英国脱欧进行第二次公投,约翰·格雷认为这是妄想的虚伪。图片来源:Niklas Halle'n / AFP via Getty Images
“我在90年代初接受了一家波兰报纸的采访,”格雷说,“他们问,‘你认为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后出现的新撒切尔保守主义会如何?’”我说,“可能和此前的保守主义差不多。从一开始,建立统一的欧洲经济体就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项目。对欧洲联盟的反弹将来自何方?肯定会来自右派,这就是事实。”
格雷预测,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中获胜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被抛弃的感觉,以及对大部分劳动人口的不尊重”一定会导致某种后果。他还认为,即使拜登获胜,这些力量也不会被消除。永远不要指望人类做出理性的选择。“正如伯特兰·罗素指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开始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这是对无聊的中止。”
猫似乎不会感到无聊,因为按照格雷的说法,它们永远不会为获得快乐而挣扎。另一方面,人类“是自我分裂的生物,我们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替换活动(指为逃避困难或不愉快但不得不做的事而做的事情)”。大部分替换活动是猫所不具有的,这些替换活动是对死亡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的产物。格雷既不是虔诚的信徒,也反对无神论。他对理查德·道金斯(英国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以及他的支持者的信念——“宗教可以轻松地被抹去”——表示不屑。
格雷认为,我们天生需要用想象力和神话来解释死亡和痛苦,这太重要了。“我对上帝一无所知,但我认为,‘人可以消除信仰宗教的冲动’这一想法是荒谬的。我曾经在美国遇到一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严肃地告诉我,如果年轻人在完全纯洁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结婚前就不会有性冲动,”说罢,格雷大笑,“这正是理查德·道金斯对宗教的看法。神话是历史上任何一种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会想象它正在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消失呢?”
格雷的这本书充斥着很强的娱乐性。在指出哲学家的更高理想与他们生活中的动物本能之间难以跨越鸿沟的时,他也采用了这样的笔调。但他拒绝以自传的方式解读他自己的生活或思想。对于很多个人问题,他有一些宽泛的辩护,如“我倾向于认为我的生活并不那么有趣”。我曾问过他是否认为没有孩子这件事影响了他的思想。在两个小时关于猫咪的泛泛而谈中,他仅用含糊、简短的一句回答打住了这个问题:“我倾向于不谈论自己的生活。”
我想知道,他选择住在巴斯的原因是否和叔本华选择在法兰克福生活相同:那里“没有洪水,但有更好的咖啡馆和好的牙医”?
他笑了。“这里的牙医似乎还不错。”在结束学术界的生活后,他去了巴斯。此前,他曾在牛津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后来又在伦敦政经学院担任欧洲思想学教授十年。如今的他来到巴斯,是为了成为“自由作家”。他说:“我想要的是一个能让我步行的城市。我喜欢这里——在这里,抬头即可看到树木。”他说,脱离学术界给了他更多的自由,他可以像猫一样随意写作。
他说:“如果你是一名学者,那么在发表任何言论之前,你必须先提出种种预告。当我还是一名专业学者时,我是那样做的。但是,现在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只需要说,我发表这个观点,仅供参考。不必摈弃它。”
他喜欢蒙田和博尔赫斯等作家的坦率,他们构建神话般的思想实验。他说:“英语世界将格言与傲慢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其他写作方式是否更能改变人们的想法。我不需要追随者。我甚至不指望能有很多人理解我的意思。我在书中所表达的全部观点是,要触发一些读者的思考过程,他们获得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对于那些认为他的作品停留表现在人类的还原性,野蛮的一面,而不是人类伟大的集体成就上的批评家们,他怎么说?“如果你也认为,文明生活就像蜘蛛网——它易遭破坏,却难以建造。那么,我写的东西也许是一记警钟。我反对狂妄自大。”
在《稻草狗》的最后一句话中,格雷悲伤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认识到,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看见?”撰写本书是否有帮助他理解这样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
他说:“猫是为了生活的感觉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实现或不实现某种东西。如果我们过于专注于某些首要目标,我们将失去生活的乐趣。将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和宗教放在一边,还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生活的感觉——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东西。”
本文作者Tim Adams系前《观察者报》资深记者。
(翻译:王宁远)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