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作家,尤拉·比斯有两大天赋。其一,她有能力向读者挑明房间里的大象,她在《无人区笔记》( Notes from No Man's Land )一书中就做到了这一点,这本文集反思了美国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她在开篇的文章中讲述了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美国白人如何抱怨自己居住的街区里架起了电报杆,直到他们发现了电报杆的新用途——作为对黑人实施私刑的绞刑架。她的另一个天赋是将我们潜藏的恐惧暴露出来,在2015年出版的《免疫》一书中,比斯追溯了疫苗接种的历史和许多美国人对接种的恐惧,并联系到了现代社会为人母的焦虑。
在《占有与被占有》( Having and Being Had )中,比斯的这两种天赋都得到了展示。她追根究底地探讨了我们对于财富、工作和财产的假想,揭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被灌输和内化的——我们是如何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认同资本主义要求的。我们在其中浸润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就像鱼儿不知道水是湿的一样。如果你已经超过40岁,曾经想过要弄清楚自己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比斯为你创造了这个神奇的按钮,然后把手指放在上面,用力地按下去。

《免疫》
[美]尤拉·比斯 著彭茂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8-1
2014年,比斯和丈夫约翰买了第一套房子。这本该是件开心的事,她却有种说不出的膈应,于是她买了一本日记,像作家一样,试图在纸上找出答案。那本日记最终变成了这本书,它以小品集的形式,记录了她作为作家和教师的工作,也记录了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所有这些都是从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的。
她阅读,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从自己一生贫苦的母亲到经济学家。对比斯来说,钱一度是用来买时间的,特别是用来买写作的时间。她一路轻快,但突然之间,她发现自己被锁进了一场无法逃脱的游戏。她必须装修房子,必须维护房子,这不仅仅是房子,更是资产。“人到中年,讲究的就是个‘维持’。”她的母亲曾这样告诉她。她所在的地区正在优化改造,一位年长的黑人妇女因为负担不起飞涨的房产税,被从她祖父建造的房子里赶了出来,她命令比斯离开她的草坪。一位银行监理在这条街上也有一栋房子,不知怎地就要把住在房子里的男孩赶走,因为警察被叫去过。“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约翰对比斯说,“他在意的是他的财产。”
为了保住房子,她必须保住工作。当个打工人,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写作了。她去见了一位财务顾问,讨论退休计划。金融工具的复杂性超出想象,而且充满了道德风险——她投资的某家公司可能员工福利很好,但却危害环境。哪一种金融工具都经不起道德推敲。“我问他这种投资体系是否有一天会终结。他说,不会,你的钱是安全的。但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这个体系能否找到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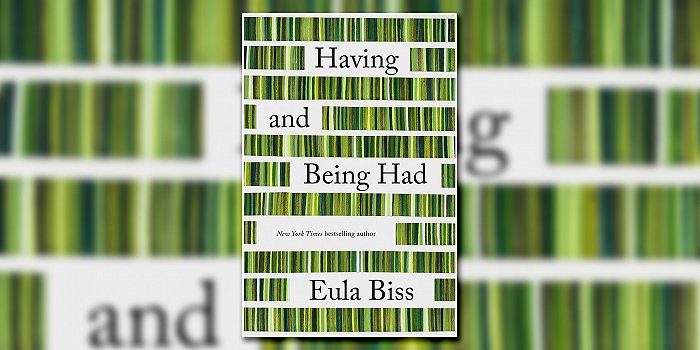
《占有与被占有》
尤拉·比斯 著
你一旦发现了消费资本主义的无孔不入,就无法再视而不见。比斯的儿子开始在学校交易宝可梦卡片,孩子们因为卡片的价值发生了争吵——而卡片的价值只在于有人愿意为它付出多少,就像毕加索的画。二战前的巴黎,佩吉·古根海姆(其父随泰坦尼克号遇难)用继承的遗产购买了当时不知名艺术家的画作。“十幅毕加索,四十幅恩斯特,八幅胡安·米罗,三幅达利,一幅夏加尔。那时德国人正向巴黎进发时,许多艺术家都急切地要离开法国,她从他们手中购买了许多画作。”许多年之后,古根海姆基金会为比斯的创作提供了资助,这才使得比斯有可能为她的房子付上首付。
工作与艺术的共生关系让人苦恼。首先你没有钱,要如何创作呢?艺术也赚不到几个钱,要如何继续创作呢?伍尔夫就曾写到过,一个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还需要一笔收入——按照今天的消费水平换算大概是七万五千英镑,另外还要配一位管家。伍尔夫对她的厨师内莉·博克索尔很不好,给她的工资又低,在博克索尔住院后还解雇了她。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保护工人不受这种待遇,曾出台过一些法规,但现在也没有了。

气候营的一顶帐篷上挂着杰拉德·温斯坦利的名言:语言和文字都是虚无缥缈的,都是死的,因为行动是一切的生命,如果你不行动,就什么也做不成。拍摄:Martin Argles
比斯和儿子一起看《史酷比》的时候,电视上的一帮人正在追坏人,而反派想用假鬼吓唬人,好让他们抓紧时间发财。操场上有一位父亲说,这个节目讲的是“失调的资本主义,是吧?资本主义出了问题。人们开始钻制度的空子”。但是,比斯认为,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吗?美国的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公平的,它总是向白人男性倾斜,也总是限制着其他群体拥有财产的权利,比如女性,比如黑人。
比斯没有给出过多的建议,只是陈述。历史上曾经有过反资本主义的叛乱,不过最终都没有成功。当然,这其中有共产主义,也有礼物经济( 译注:指提供商品或服务者并不明确地要求回馈,施与受之间没有规定的义务关系,是对“人的行为都是经过理性计算”的驳斥 )。掘地派产生于17世纪中叶内战后的英国,“他们的计划是把食物送给每一位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并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不是封建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最终,掘地派逃离了英国,来到了美国,但在美国他们的思想早已被遗忘了。
“一个人如果二十岁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是没有良心;而如果到了四十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头脑。”这句话丘吉尔和约翰·亚当斯都说过。如果你在读完《占有与被占有》后还没有深感不安,你肯定也是没有良知。
(翻译:都述文)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