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厅》三部曲第三卷刚一问世,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Hantel)就回到了德文郡的书房,与演员本·迈尔斯(Ben Miles)远程合作编剧,给《镜与光》( The Mirror and the Light )的话剧改编赋予新的生命。她说,第一场朗诵会即将举行,但由于无法面对面交流,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合作,“所以我们必须成为对方的合格办事员。”
在曼特尔成为这个世界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前的几十年里,她将小说辛苦和贫穷的本质与文学为生活赋予的相对轻松的气质结合在一起。“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批评训练,所以我的写作风格更轻快和风趣,而不是学术性的,”1987年,她这样写信给《伦敦书评》的编辑卡尔·米勒(Karl Miller)。
这封早期的手写信是30多年来曼特尔与卡尔·米勒之间通信来往的第一封信,给曼特尔为《伦敦书评》写的新文集《曼特尔碎片》( Mantel Pieces )打下了基础。“《每日快报》的记者正坐在我家外面,电话铃响着,等等……这些都是充满讽刺的悲伤日子。”2013年,她在文章《皇室身体》(Royal Bodies)里追溯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和凯特·米德尔顿(Anne Boleyn)的故事,在发表后引发差评,促使她发来了这封邮件。她写道,这位英国未来王位继承人的母亲,“似乎是由一个委员会设计,由工匠打造的。她有着完美的塑料笑容,四肢的主轴是手工转动的,并经过光洁的抛光。”
《曼特尔碎片》包含了二十篇文章,其中许多作品都反映了她对于女性身体在历史中地位的持续关注,从1988年对雪儿·海蒂的《海蒂性学报告》的抨击开始(“世界上一半的小说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但海蒂想把它定性成一个科学事实”),到2017年对历史上失去姓名的女性的沉思,灵感来自于一幅平庸的肖像画,画中人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都铎时期的女伯爵玛格丽特·波尔(Margaret Pole)。(“当你需要他的时候,汉斯·霍尔拜因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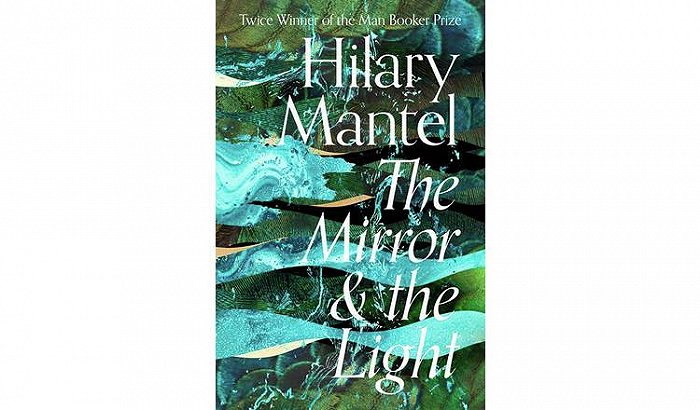
《镜与光》
今年曼特尔和丈夫始终待在家里,因为两人都有较高的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在此期间,她在自传《放弃幽灵》( Giving Up the Ghost )中动情地记述了她与自己身体的斗争,她的文章也揭示了这种斗争对她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持续影响。“如果像我一样,你在27岁时接受了停经荷尔蒙治疗,你就会思考生育和更年期的问题,以及没有孩子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一切都灾难性地发生了,”她说。
“这也意味着我意识到女性在医学界遭到了怎样野蛮的对待:她们的痛苦没有得到控制,她们的声音没人听到。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要么‘她挡了我们的路’,要么‘她抱怨太多’,要么‘她说话太多’,或者——以玛格丽特·波尔为例——她的子宫有问题,她在繁衍后代。所以是的,我认为女性身体的问题化是一个主题。我不希望人们认为这就是我不断写的东西,但这无疑是个阴影。”
虽然三部曲的中心人物是一个男人——托马斯·克伦威尔,但这是一部由女性身体推动的历史,尤其是不幸嫁给亨利八世的六个女人。第一卷主要讲述了阿拉贡的凯瑟琳,第二卷讲述了安妮·博林和简·西摩,而第三卷讲述了克莱维斯的安妮。不过,正如曼特尔在下文中向露丝·克罗斯(Ruth Cross)保证的那样,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她对这位被抛弃的德国公主的描述“与别的版本不一样”。
在《观察者报》读者提交的许多“可爱”的问题中,她对那些回溯到她之前的当代小说《黑夜之外》( Beyond Black )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这部小说讲述了被鬼缠身的超能力者艾莉森的故事。“从许多方面来说,它是三部曲的初步尝试,这个故事考量的是人们与个人历史的关系,以及与更大的历史的关系,”她解释说。
“在艾莉森这个角色中,各种皇室人物都会一闪而过,尽其所能熬过去,最终的命运仍是不受认可。我不是说公众对历史不感兴趣,但他们认为有一个叫做真相的上锁的箱子,只有历史学家才有钥匙。这就不允许死者活着——他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们是可以被解读的。”
这是一个有力的隐喻,曼特尔自己也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唤起被遗忘的以及熟悉的鬼魂,输出到世界各地,不仅在她的小说中,而且在戏剧和电视中。“死者有很多不同的类别:那些不断被加工的人物,还有那些被历史所熟知的人物,但他们的名字并没有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她说,”我喜欢把他们想象成曼哈顿的空气——那似乎是一件非常美妙而强大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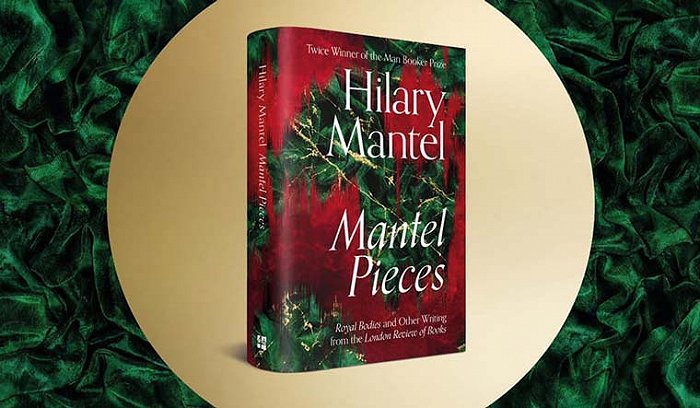
《曼特尔碎片》
凯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小说家
这是一个作家对作家的问题。我很乐意只写作但不发表作品(我从未听其他作家这么说过!),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或者说让别人读你的文字能丰富你的写作?
曼特尔: 我刚刚在读弗洛拉·马约尔(Flora Mayor)的《校长的女儿》( The Rector's Daughter ),女主人公在书中写道:“几乎是像蚕织茧一样,从没想过要去欣赏。”我不是蚕。我发现出版很难,到了某个点的时候,我也不会坚持——我想如果我的第二部小说没有被接受,我就会断定我没有市场。之后,我可能会偷偷摸摸地写,我忍不住要写下几个短句。我觉得把想法写下来很容易,但我可能需要读者(和金钱)的诱惑来见证我完成整个故事。
露西·休斯·哈勒特(Lucy Hughes-Hallett),历史学家和小说家
**在你的小说中,死者会说话,无论是通过灵媒传递信息,还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监狱墙壁上向他低语的石头。你认为我们与死者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欠他们什么(如果有的话)? **
曼特尔: 对于克伦威尔来说,他无法利用精神分析的词汇,死者从过去的自己身上给他的现在带来了信息,并提醒他关于自己已经错过的方方面面。他的意识被不断变化的记忆穿插,他更愿意将这些记忆抹去以适应当下,但死者却像流浪狗一样在门前唠叨、哄骗、抱怨。不管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如何,我从不觉得他们能带来慰藉。我从小就相信,死掉的我正在经历炼狱的痛苦——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它始终都在。
汤姆·霍兰,历史学家
**法国大革命是特别适合年轻人的话题吗?宗教改革是特别适合中年人的话题吗?如果是,你觉得哪些历史时期可能特别适合老年人? **
曼特尔: 年轻人更容易感受到革命的必要性,见过的失败案例也比较少。他们不服输,也不相信宿命论。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时机,也能理解为什么法国人没有耐心坐等下一代人去改革。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如果愤世嫉俗或感到厌倦、觉得人类的可能性已经耗尽,那么她就会失去力量。你必须出于一种信念来写作,即事情可以不同、可以更好。
我想说,宗教改革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虽然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想到了托马斯·克伦威尔,但那时我不可能写他。看看他的画像就知道了,他经历过太多了。
真正的老人应该回归神话,和罗宾一起住在绿林里,窥探那条据说会向正义弯曲的弧线。
阿曼达·福尔曼(Amanda Foreman),历史学家
**我一直想知道你是如何创造小说的结构的。《狼厅》系列写得像一张蜘蛛网,你是怎么做到的? **
曼特尔: 如果你去想一想任何有价值的小说——交错的故事线,交织的主题和隐喻——没有人足够聪明到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你的脑袋里塞满了数据,你就必须把手拿开,看看故事自己会变成什么形状。你必须相信这个过程,这可能很困难,因为你必须平息焦虑,因为你的任务是不要挡了自己的路。我认为这对所有有价值的小说都是如此,不仅仅是历史小说。你作品的中心是对小说形式的信任,你运用的是济慈所谓的“消极能力”——你必须忍受怀疑,走上一条没有路标的道路。
当然,在准备阶段,你会需要所有的智慧、彻底的投入、一切的记忆资源。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无法设计小说,也不能够操纵它。你可以倾听它的声音,为它腾出一个空间,远远地为它找到合适的方式。
(翻译:李思璟)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