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贝卡·索尔尼是艺术、文化和政治领域的著名作家之一,被《纽约时报》称为“抵抗的声音”。她此前著有23本书,包括《浪游之歌》《黑暗中的希望》和2008年的随笔《爱说教的男人》等——后者催生了“直男癌的说教”(mansplaining)一词的出现。她的新书《回忆我的失语生活》( Recollections of My Non-Existence )是一本关于她在旧金山度过的早期作家生活的回忆录,她在那里生活了40年。
你的写作总是基于个人经历的,为什么你决定此时正式写作一本回忆录?
索尔尼: 在多年写作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对女性声音的压制等女性主义随笔之后,我感到还有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我尚未触及,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心理影响——即使你不是最糟糕情况的直接受害者,但你仍然生活在这个制度中,其中针对女性的暴力如此普遍,环境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我想以自己作为一个案例研究,即使某个女性不是最悲惨的直接受害者,她仍会受到制度和环境的深远影响,书中呈现的正是这样的生活。
你感到男性暴力的威胁如此普遍,导致你有时想要隐身——本书标题就源于此吗?
索尔尼: 我认为,年轻女性的想象中充满了持久的恐惧:“我不能穿这个,我不能去那里,我不能这个时间出门,我不能相信这个人,我必须小心这是否会导致某种不适或危险……”我想将这种恐惧与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即对女性自主掌控和选择权的攻击(干扰)也存在于其他更文明的场域(例如出版业)中。因此,它是关于我如何找到自己声音的个人故事,同时讲述了在一个不希望女性发声的社会中身为一名女性的普遍故事。
《回忆我的失语生活》
相比你以前的作品,写作这本书更艰难或更使你痛苦吗?
索尔尼: 并不算很痛苦,只是觉得这是一本非常质朴的书,所以某种意义上,它是丑陋的,我在书中谈论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坏的经历,但我的本能是想呈现一些美好的东西。这很有趣,因为这本书非常个人化,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是否具有任何意义。
你曾成长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但在本书中你为什么没有很详细地描写?
索尔尼: 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谈论家庭暴力的文化,并且已有很多关于童年虐待的回忆录。我对这一主题并不很感兴趣,对此也没有什么新发现。我反而觉得,人们并没有讨论过我在这本书中真正想谈论的内容,即“环境骚扰”(ambient harassment,指并非直接受害者,但因目睹周围环境中的骚扰而成为间接受害者)的威胁,所以我从自己的19岁写起。
你当时预感到了你的随笔《爱说教的男人》会吸引如此多的读者吗?
索尔尼: 完全没有。我不知道它会让这么多人共鸣,因为我所写的经历平凡又使人愤怒。不仅是使人愤怒,它简直阻碍着女性说出私人经历中的真相,或在其职业能力上受到尊重。通过结合我的个人知觉和切实的普遍经历,我无心插柳地写出了某种东西——它在许多女性的生活中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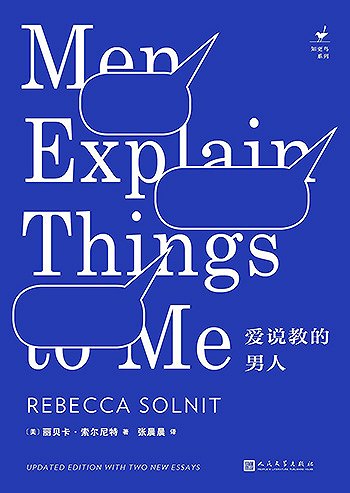
《爱说教的男人》
[美]丽贝卡·索尔尼特 著张晨晨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
那篇文章传播得飞快,你是否认为社交媒体赋予了人们良好的发声渠道?
索尔尼: 我觉得自己从来无法权衡这把双刃剑。我认为,谷歌、推特和脸书的所有者选择去侵犯人们的隐私、用我们的个人数据获利,他们选择了容忍误导性的宣传、虚假信息和选举腐败。回到“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时期,很多有良知的人都使用了社交媒体发挥好的作用,但从中获利的所有者根本不在乎人权和民主、平等发声和信息的准确性。唐纳德·特朗普能成为美国总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我认为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社交媒体及其创造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误导。
你2016年的作品《黑暗中的希望》鼓舞了伊拉克战争期间以及特朗普当选后的进步主义者。你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吗?
索尔尼: 我曾是个很沮丧的年轻人。后来我希望成为一名活跃人士和写作历史的作家,为人们带来希望,去看到世界比我们以为的更好,看到普通人其实可以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能够借助这股力量使世界更美好。但我不得不说,过去的几年让我有点儿失望,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和唐纳德·特朗普,还因为导致特朗普现象发生的那种集体式疯狂。
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你的英国之旅取消了。在低落期,你会从哪些作家或艺术家那里寻求鼓舞?
索尔尼: 我认为有一些作家和诗人很鼓舞人心:我阅读杰克·吉尔伯特、罗伯特·哈斯、菲利普·莱文。我还总在寻找周遭发生的蕴含着可能性和积极因素的事情,例如人们如何在隔离期间互助团结帮助。我本来非常期待英国之旅,非常期待与英国学者玛丽·比尔德爵士对话。只要可能,我一定会尽快去英国,并与比尔德爵士会面。
本文作者Stephanie Merritt是前《观察家报》文学副主编。她也是一名作家。
(翻译:西楠)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