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戴安娜·索哈米所认为的,女同性恋远不止是一种性取向:它延伸到艺术职业、情感崇拜和政治运动,也挑战了那些认为“女人身体属于男人”、应该被奉为神圣、以延续男性血统的观念。索哈米曾写过几本被杜鲁门·卡波特 称为“菊花链”(daisy-chain)和“假小子”(butch-babes)的优秀传记。如今,在新作《没有女同就没有现代主义》( No Modernism Without Lesbians )中,她将20世纪早期的艺术、礼仪和道德现代化归功于女同性恋者们。
就像小报的头条一样,索哈米的标题是为了吸引人,它依赖于一个有点微妙的类比:“现代主义艺术颠覆了19世纪形式和叙事的规则。”为什么现代生活不应该修改“性交易行为准则”,许可女人拒绝男人,或允许她们彼此相爱呢?如果用更温和的方式来解释索哈米的观点,那就是如果女同性恋书商西尔维娅·毕奇(Sylvia Beach)没有安排在巴黎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现代主义可能就不会出现——当时伦敦和纽约的编辑担心被指控出版淫秽作品而拒绝出版这本书。
毕奇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她对乔伊斯的态度忠诚,而这正是乔伊斯的妻子——诺拉·巴纳克尔(Nora Barnacle)所真正缺乏的。她乐于执行乔伊斯无休止的编辑琐事,并称赞这项工作是她的“传教事业”。但当更富有的赞助者出现时,乔伊斯自然而然选择忘记了毕奇的辛劳。这是女性合作者很难摆脱的命运。毕奇的书店以前是个洗衣房,是一个家庭空间,里面摆放着舒适的椅子和花瓶,热心的毕奇还会给买不起茶或书的顾客沏茶或借书。
索哈米笔下的另一个人物则在更大的范围内施惠。布赖尔——原名安妮·温妮弗雷德·格洛弗,尽管她从锡利群岛借用了一个新名字来改名换姓,但她依然是一位航运大亨慷慨大方的女儿。布赖尔资助了她所认识的艺术家的异想天开:向弗洛伊德付了一笔小钱来对她的爱人希尔达·杜利特进行心理分析,送了伊迪丝·西特韦尔一所房子。在更神圣或更恍惚的时刻,她会对街上的陌生人慷慨大方:她为一个在排队买面包时发现牙齿掉光的女人买了新假牙,还替一个可怜的消防员更换了不合身的惠灵顿长筒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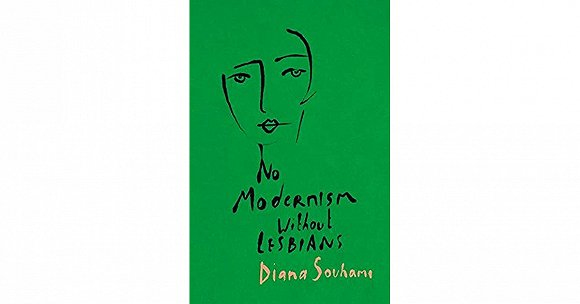
《没有女同就没有现代主义》
在书中,索哈米抨击了导致战争、大屠杀和性压抑的“旧式男性统治”。1940年,当穿着长筒靴的侵略者进军巴黎,践踏曾经的“西方世界的萨福中心”时,她称父权制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然而,权力并非专属于男性,也潜伏在书中所考察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中。画家兼诗人娜塔莉·巴尼以一个鲁莽的掠食者的形象出现,她在扑向一个仰卧的诱惑者时弄坏了沙发。另一位女继承人,波利尼亚克公主维纳雷塔·辛格,她的自由解放是由家族生产的缝纫机资助的——用金钱把善变的社交名媛维奥莱特·特雷福西斯绑在身后。
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则表演了这种权力游戏的一种矛盾变体。斯泰因脾气暴躁,粗声粗气,而托克拉斯,尽管留着小胡子,却显得温顺而文雅。爱丽丝料理家务,做饭,让格特鲁德成为专职天才,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你得整天坐那里无所事事”。然而,正如海明威所言,这个家庭中的弱者却是奴隶主,他无意中听到斯泰因被她称作“猫咪”的爱人用言语猛攻时,不得不向其求饶。
斯泰因通过“20世纪的文学就是格特鲁德·斯泰因”来宣告自己的艺术地位,弥补了这种卑躬屈膝的情绪。不过事到如今,她的自欺欺人听起来很荒唐,索哈米她视为“现代主义之母”的观点也并不更有说服力。斯泰因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女贵人——像毕奇和布赖尔一样,她开了一个沙龙,在那里她扮演传统的女主人角色,监督出席的男画家、作家和音乐家之间的同志情谊。她从旧金山的有轨电车行业获得了惊人收入,并用这些收入收藏了塞尚、毕加和索马蒂斯的画作,价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她没有把这些画装裱起来,有时还随意地把它们藏在壁橱里。
被斯泰因单调乏味的史诗《美国人的创造》唬住的索哈米,在维吉尔·汤姆森的全本歌剧《三幕剧中的四圣徒》中,有幸为自己的歌词配上了鸟儿般的低吟。在这其中,斯泰因的语言动作被融入到音乐中,而索哈米则写出了这个机智却空洞作品的神韵。然后,她过分热情地宣称,《三幕剧中的四圣徒》比《尤利西斯》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创新性,只是因为乔伊斯的小说仍然古板地“被一本书的封面所束缚”。
索哈米以对斯泰因轻快的模仿而结尾,在巴黎的天堂里,“爱与生活中的恋人们依然相爱,爱着的人和被爱的人依然相爱。”我缩短了一段长长的哈利路亚般的押韵段落:这正是卡波特所说的“菊花链”,但这些重复很难抹去索哈米悲惨童年和痛苦回忆。爱是可爱的,是神圣的,但性——无论哪种性别——都有着恶魔般的力量。
(翻译:张海宁)
 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